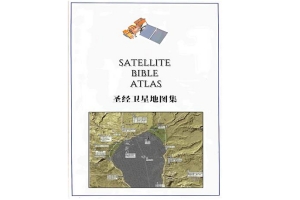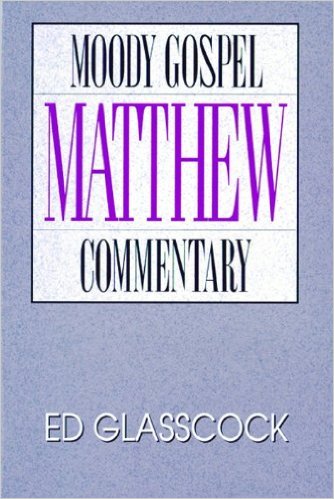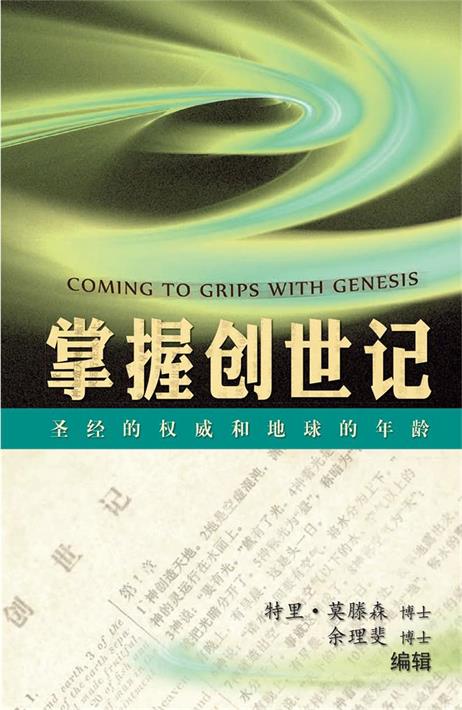
第二章:创世记第1-11章解经概述:从路德到莱尔
大卫·W·霍尔(David W. Hall)
乔治·山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曾经写道:“那些不记得过去的人注定重蹈覆辙。” 一些学者似乎也避免不了这种重复过去的错误或错谬观念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最明显的一个学术领域就是基督教学者对历史的评估,特别是针对创造和相关的问题,关于谁在什么时候确认了什么。沃尔特·凯泽(Walter Kaiser)就是众多例子之一,他认为,“长日论自公元四世纪以来一直是教会的多数观点”。[1]
为了澄清许多没有查证的引述、市井传说以及对著名思想家赤裸裸的断章取义,我们整理了19世纪中叶教会放弃传统观念之前对创世记第1-11的释经史,希望能够成为学者或对正确释经感兴趣者的有用资料。
有这样一个市井传说:在基要派和现代派论战正酣的时候,被动的年轻地球福音派人士炮制出从无到有的字面六日创造论。德州农工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麦金太尔(John McIntyre)因此警告所谓的“基督徒失忆症” —— 声称人们忘记了早期的解经家们对创造的观念:“(有些)基督徒引进了现代的、天真的观念——以24小时解释创世记的一天,与奥古斯丁、阿奎那和加尔文对创造日的经典而细致的分析背道而驰。今天的基督徒学者怎能如此彻底地忽略之前伟大的基督教学者?”[2] 本章旨在挑战麦金太尔的判定,并专注于宗教改革之后的历史,因为穆克在前边的一章已经讨论了宗教改革之前的历史。
因此,以下的总结包括了自1500年到约1830年间(大约是深度时间地质理论的领袖人物查尔斯·莱尔的年代)最著名的神学家的观点。我们要表明,这些神学家对创世和地球年龄的观点基本一致。[3] 我们认为,在1800年以前的基督教文献中很难找到既采用严格的解经方法,又捍卫非字面解释创世记1-11的著述。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联想到路易斯(C.S. Lewis)的多彩用语“时代势利眼”。通常,很多人在讨论中似乎已经先入为主地贬低早期基督徒,仅仅因为他们是早期的(或“前科学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明智地注意一些“重新发现”古老正统的人所带来的挑战。如果他们反对历史上相当令人信服的、早期作者的释经共识,就更当重视。因此,我们认为,今天福音派对创世记的完整解释不仅要求持守圣经无误,而且要求更严肃地考虑创世记第1-11章的解经史。
我们只能猜测,为什么不信的人通常比基督教的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在承认这一点上更具有客观性。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尽管有很强的反基督教偏见,但是他观察到一条历史悠久的解经路线:从阿奎那到加尔文,人们都坚持遵循了字面解经的原则。[4] 怀特在19世纪后期不得不承认加尔文对“创世记”有一个“严格的”解释;而且“几乎直到我们这一代人开始记事时,这一解释‘始终被各地各方所有的人’所接受: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宇宙是直接由全能者的话音、双手或话音加双手从无到有地在瞬间或6日内创造出来的。”[5] 既然有很多像这样的无可争议的见证,为什么一些现代福音派人士还是继续歪曲事实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当我们从整体上考虑第一手资料,而不是盲从当代古老地球创造论倡导者的无稽之谈时,我们会看到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约翰·卫斯理等人都不是深度时间或渐进创造论的朋友。他们的声音几乎是一致的。他们是明确的正意解经,截然不同于地质学禁锢下的私意解经。过去200年的均变论地质学扭曲了人们对圣经的解释。硬说从路德到莱尔的大多数解经家的信念都与140亿年的宇宙兼容,实在是篡改历史的一个令人尴尬的极端。
新教改教家
马丁·路德的观点明确得几乎无可争议。[6] 大量文献表明,他清楚而坚定地持守字面创造日、在人堕落前没有死亡或自然之恶、及全球性洪水。[7]但值得一提的是路德(1483-1546)在更多的时候不是被歪曲地引用,而是被完全忽略。忽略路德(及其他人)作为参考点有力地说明了研究人员的选择性偏见。罗伯特·莱森(Robert Letham)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证实,路德“毫不含糊地接受了二十四小时创造日的解释,同时又极力为六千年的地球历史辩护。” [8]
在加尔文的著作发表之前不久,英格兰教会主教休·拉蒂默(Hugh Latimer,1485-1555)表达了他认为代表了当时的基督教世界的观点。他的圣经注释把字面理解创世记第1章看为理所当然。在1552年的一次讲道中,他用这些发人深省的话语告诫听众:“既然知道这个世界只会存留一点点儿的时间,我们怎么能如此地愚蠢,把这个世界看得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从圣经中知道,所有有学问的人也都肯定这一点,那就是世界被造出来只要持续六千年。现在,在这六千年中,有五千五百五十二年已经过去了,而且,这剩余的时间会为选民的缘故而缩短,正如基督本人所做的见证。”[9] 一个星期以后,他再次劝告听众反省他们的所为,因为“圣经和所有学识渊博的人一致同意,在神的命定中,这个世界要延续六千年。现在,这一数目已经过去了5552,所以只剩下448,这不过是一丁点时间了。” [10] 除了这个减法运算,我们还应该听到他的弦外之意:拉蒂默显然相信按创世记载的字面意思来计算的时间。他从自己的前提(地球的年代)轻易地就转到警告,这实在让人吃惊。但是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他声称所有“博学的人都同意”。他应该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了解他的同代人对创造的看法。
因此,声称中世纪晚期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徒并不坚持特别创造论,这是篡改历史的做法。仔细检查就发现该主张是站不住脚的,是相对近期的观点,是为了适应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不是为了历史的准确性。在莱尔之前,不可想象忠实的基督徒们会建议创造可以发生在神命令的话语之外,更不用说发生于数个不确定的漫长时期了。正如罗伯特·毕晓普(Robert Bishop)所言:“这卷书(创世记)的原始读者和直到200年前的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地质时代’的概念。”[11] 在19世纪之前,与宏观进化兼容的创造论观点即使存在,也属凤毛麟角。
霍华德·凡·提优(Howard Van Till)等人声称,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所持守的思想与现代科学的发现很兼容。[12] 然而,仔细审查就可以看出,这和古老地球倡导者对教会先贤作品的扭曲如出一辙。加尔文对创造有个一以贯之的看法,他明确地说,“神,靠着他的话语,是宇宙的创造者。”[13] 他还肯定 “摩西对创世的历史所作的见证的确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神从“无形之物”创造。[14]
加尔文没有提倡“持续创造”作为妥协的模式,而是指出:“我们被吸引离开其他虚构的故事来到独一的神面前,他将创造之工分配到六天的时间里,好让我们即使终生默想,也不至于厌烦。” [15] 他反复并一贯称摩西为“独一神和造物主的可靠见证人和先锋”。 [16] 加尔文还写道:“创造不是从外部倾入,而是物质从无到有的发源。”[17]
加尔文在他关于创造的主要释经著作中,首先指出他同意以前巴西流和安波罗修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加尔文在总结“摩西简短叙述的关于宇宙创造的最初历史”时指出: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神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的力量从无到有地创造了天地,并在其上造出了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在一连串精彩的活动中,他将万物分门别类,赋予每一类独特的性质和功能、指定的场所和位置。”[18]
他的讨论目标是实践性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不仅要让信徒知道关于创造的真理,而且要引导他们来赞美造物主。神是大能的,他要造出我们周围所有的美丽世界,六天的时间绝不是太短,加尔文断言:“因为将宇宙的创造分成六天自有其意义,对于他来说,在一瞬间完成整个工作的所有细节并不比这样分步完成来得困难。” [19] 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并不支持渐进进化论或神导进化论,也不支持从已经存在的物质进行创造。
加尔文的观点可以从他在圣经注释中对关键经文的解释而得到进一步证实。在对创世记1:1的论述中,他这样解说:
“当神起初创造天地时,地是空虚荒芜的。并且,他用‘创造’一词教导说,以前不存在的东西还没有被造。所以他的意思是世界是从无到有地受造的。由此就驳斥了那些人的愚昧,他们以为未成形的物质是永恒存在的,他们从摩西的叙述中只看到世界被装上新的装饰品,并且得到了之前所缺少的形式。”[20]
在谈到创世的第五天时,加尔文观察到,即使神从已经存在的物质中塑造了新生命,也是值得称颂的:“因此,他命令地生出这些东西来,这一神迹与凭空造出这些东西来同样伟大。而且他从地球上取材不是因为他需要这种材料,而是为了更好地将世界的各个部分与宇宙本身结合起来。”[21]
加尔文对希伯来书11:3的注释:“因为有信心的人并非仅仅有一个关于造物主上帝的见解,而是头脑中有深刻坚定的信念,并且仰望真神。再者,他们了解神话语的大能,这大能不仅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即刻彰显,而且也在维护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彰显 。” [22] 关于这段经文,他曾指出“即使异教徒也承认”创造。[23] 关于以赛亚书40:22,加尔文观察到:“他以前讲到世界的创造,但现在他论及世界的持续治理;因为神不仅在短时间内发挥力量创造了世界,而且他通过维护世界同样有效地表现出自己的力量。这一点值得注意:如果神没有持续地伸出手来托住万有的存在,那么我们的头脑中对于上帝是造物主也不会有深刻的印象。” 在该语境中,加尔文非但没有贬低神短时间的创造,反而大加颂扬; 但他也敦促圣徒不断认识神和他的治理。
有趣的是,如果加尔文想提倡“漫长的年代”,他完全可以使用今天的长日论倡导者所经常使用的两节经文:诗篇90:4和彼得后书3:8。但是,加尔文没有提出创世的几天可能长达千万年的想法,他认为这些段落只是意味着神是超越时间的。
加尔文在1554年的解经著作中讨论到创世记1:5时发表了关于神迁就的著名说法,这让有些人猜想:如果加尔文今天还活着,他将是创世记第1章的非字面解释者。但是仔细分析,他的文字并不支持这种臆想。他写道:
“那些人的错误在这里被明显地驳斥了,他们坚持认为世界是在瞬间造成的。说摩西仅仅为了传达教导的需要就将神一下子完成的工作分配到六天之内,这实在是太过牵强。让我们宁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神自己花了六天的时间,目的是为了让他的工作迁就人的能力。”[24]
他有意识地拒绝了奥古斯丁的观点,[25] 表明在他的思想中,创世记不只是一个用于教导神学的文学框架,而是记录了那几日神的“作为”。此外,他在该著作的其他地方确认(1)光是在太阳和月亮之前被造的;(2)第2天将水聚在一处是一个神迹;(3)他在第四天创造了众星;(4)亚当是实实在在用地上的尘土造出来的,(5)大洪水是全球性的,(6)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是严格的纪年表(没有间隔)。[26]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加尔文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始终如一,这与现代人企图将亿万年的历史嵌入创世记载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加尔文的副手西奥多·贝扎(Theodore Beza,1519-1605)也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确认希伯来书11:3所讲的是“从无到有”的创造。[27]
在查阅了早期新教领袖加尔文、贝扎和路德的著作之后,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观点总结如下:
创世记1-11的本意就是按字面理解的历史
这些人采用了正常的释经学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宇宙的历史不到6000年
他们持守字面的天
从加尔文到乌雪(Ussher)
在加尔文死后(1564年)的一个世纪,众多改革宗神学家[28] 回答过现在经常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仍被当作接受创世记1-11的传统解释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当代神学家们不晓得我们的解经前辈已经很好地处理了这些反
对意见,只不过这些反对意见因着现代科学革命而变得更加突出。以下要研究的问题代表了让许多人觉得必须修改解经方法的一些所谓困难:
1. 改革家们是否回答了光在第一天被造,而太阳直到第四天才被造的问题?
2. 他们是否将自然过程作为创造的主要手段?
3. 他们是否定义了“日”的含义?
4. 他们允许长时期的创造过程吗?
5. 他们是否都认同某个特定的时间表?
6. 他们的著作是否仅反映了个人对创造的看法,还是在这一时期对创世记有正统的解释?
有几项研究罗列了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会就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统一和明确的见证(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隐含的)。[29] 当然,很难想象在1643年至1648年的委员会会议中,这些解释者“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一个解经共识。博学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会是漂流在一条释经的河流中间,他们当然不是生活在释经的真空中。包括加尔文和其他主要改革家在内的解经家们比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会早一个世纪。而在威斯敏斯特会议结束之后,其他改革宗的解经家们坚持创世记 第1章的经典解释至少又有1个世纪之久。由于较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神学委员们各自撰写的论文内容,因此这里有必要提供一个大背景,为下面的讨论铺路,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前人的研究。我们将继续检验我们的假设,看看那些17世纪的神学委员们是否将新的解释强加于教会。与其前一个世纪和后一个世纪的解经家相比,我们看到的是步调一致还是百家争鸣?因此,下面要向读者展示1540年至1740年间代表性的改革宗神学家们的评论。
此外,在加尔文之后,一批优秀的日内瓦学者留下了对上面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答案已有备案的事实应该可以说服参与辩论的现代人,这些反对意见既非没有答案,也不是新颖的。类似的挑战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经常被吹捧为传统年轻地球创造论的丧钟。但是,一经检查,学历史的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拦阻早在很久以前就已被仔细衡量过,且已发现其力道不足。
1562年版的《日内瓦圣经注释》(Annotations from the Geneva Bible)对有关问题提供了权威性的评论,并且这是在加尔文还活着并大有名气时写下的。关于创世记1:3,日内瓦圣经注释者们(当然也代表了与“新教罗马”相关的许多其他释经家)提供了对创世记载的最早的英语解释:“光是在太阳和月亮之前被造的; 因此,我们不能将那只属于神的归属于受造之物,太阳和月亮只是神的工具。”
但还是有人认为,太阳被造之前的光是创造论者难以克服的困难,这真是不可思议。早期的改革宗解经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他们只是区分了创世第1至3天来自未指定光源的光和从第4天开始发出的太阳光和月亮光。前三日在长短上没有不同,只是光源与自创世第四天以来人类所观察到的不同。早期的日内瓦解经家们欣然接受这是个神迹。他们也对创世记1:8进行了评论:“因此,我们看到仅靠神话语的能力就使地球变得丰富多产,这地球原本是贫瘠的。”[30] 现代古老地球妥协派必须证明,《日内瓦圣经》中的这些注释并不代表当时广为接受的观点。
加尔文在他的《诗篇注解》序言中表达了对沃尔夫冈·穆斯古勒斯(Wolfgang Musculus,1497-1563)的尊重,在那里他特别称赞了马丁·路德和沃尔夫冈·穆斯古勒斯。穆斯古勒斯的著作对释经家的影响超过了一个世纪。1554年,穆斯古勒斯撰写了一篇关于创世记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In Genesim Moses Commentarii Plenissimi (对摩西创世记的完整评论)。论到创世的第四天时,他解释说:
“有太阳之前就有白昼,正如有月亮和星星之前就有夜晚……那几天有莫名的光,看不到时辰的记号,甚至不知何时是正午,这些征象(根据我们的经验)是由太阳的路线决定的,并据此排列和记录的。因此,把一日与太阳相关联是正确的,因为我没有说太阳形成了一天,而是它组织并安排了一天。不过,我并没有与这里的要点相抵触,我理解创世之工不是随意的日,而是自然的日:不仅是太阳日,也是月亮和星星的日……一年之内月球完成公转十二周,即十二个月。太阳年是太阳返回到其自身循环起点的时间。”
关于创世记1:1,穆斯古勒斯注意到神是在“第一天”开始创造的。关于创世记1:3,穆斯古勒斯回答了为什么使用“晚上和早晨”这一短语的疑问,他说晚上不是结束,而是“自然日”的开始。此后不久,他便澄清说晚上是“一天的平常部分,先有晚上然后是早晨。” [31] 他还论证说,在利未记23章中,摩西将前一个晚上与安息日联系起来,作为七日之一。他解释说,出于这个原因,犹太人认为自然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穆斯古勒斯同意巴西流数算时辰的方法,不是a termino ad que,而是a termini a quo。[32] 与巴西流(和其他初期教父)一样,穆斯古勒斯认为希伯来人的时辰计算是从第一个时辰的开始而开始的,而不是从第一个时辰的结束而开始。他还提到约翰金口(Chrysostom),此人在《创世记讲章之四》(Fourth Homily on Genesis)中表示:“然而,早晨是晚上的结束,是一天的完成。” 穆斯古勒斯显然认为东正教教会持相同的观点,并没有异议,并补充说伦巴第(Lombard)也确认“早晨”不是一天的开始。穆斯古勒斯一贯把创造日解释为自然日:“因为自然日是由晚上和早晨这两个部分组成的,以便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为期三天的时间是在三夜三昼之后结束。”
他进一步补充说,整个世界的创造是在第六天完成的:“因此,天数就是时间。” 他写道,这些天是“时间上的”而且“整个世界都是在6天的运转中形成的,时间一直持续。” 穆斯古勒斯的大部头释经著作当然是当时的神学范例,他似乎并没有显示创世的日子在长度和性质上有什么分别,也没说第四日开启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新纪元。
他认为,每天都“被分为昼夜,(晚上)变成早晨。”应当像理解诗篇55:17那样理解“晚上和早晨”:“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穆斯古勒斯认为没有理由人为地把漫长的时间强加在创世的几天里,他说:“就像一个自然的白日,不是夜晚,被称为一天”,所以只要一昼夜之中有光充填,晚上和早晨就会不断重复。[33]
在现代理论出现之前很久,穆斯古勒斯就认识到在有太阳光之前就有光。他还承认,创世之前的时间不能被简单地理解。尽管如此,他和大多数同时代人都从逻辑上推断创造是在秋天,创造的第一年是“12个月的时间”,就像对年和日“在时间上”的理解。[34] 他知道任何通过观察得出的困难最终可以通过以下简单命题解决:“太阳不是光的源头。” [35]
彼得·马特尔(Peter Martyr,1499-1562)是欧洲大陆和英国最强大的改教家之一。马特尔在154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晚上和早晨在头几天光的收回和释放中形成,这是在太阳被造之前。” [36]他还作证说,“当我们谈论事物的创造时,我们不会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说一件事物形成另一件事物,而是我们确信所有自然界以及没有肉体的身体(天使、鬼魔)都是从无到有被神创造的。”[37] 对现代解经者有益的是,马特尔驳斥了两个新近的观点:(1)他确认,在太阳被造之前的头几天,包括傍晚和早晨,是通常的天;(2)他拒绝接受创造必须使用亚里士多德的特定力量或使用“神的话”以外的任何力量。他的观念是如此地明晰,使人对他的立场几乎没有任何猜测的余地。
马特尔的观点与后来乌雪大主教对神以话语创造的评论基本相同:“神是如何以及以什么方式创造万物的? 绝不是使用任何手段或工具(他不像人一样需要这些),而是凭着他有能力的话语,就是凭他的独一意志,叫那些不存在的东西成为存在的东西,希11:3,罗4:17,诗148:5。”[38]
马特尔,远非缺乏启蒙,接下来讲到了几百年之后敌对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他指出:“因为神,为了表现出他的大能和怜悯,从无生有地造出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并造出几乎无限的人。” 像马特尔那样的早期正统神学家并不认为创造是仅仅依靠自然过程或主要依靠自然过程,而是相信以下几点:“把水与地分开,我们不归功于星星,而是归功于神的圣言,让地上长出植物和菜蔬的力量也是如此……尽管圣经记载说水要滋生或地要长出这个或那个,然而万物的创造之功必须单单归于神。” [39]
另一个与加尔文同时代的日内瓦人,伟大的法学家弗朗索瓦·霍特曼(Francois Hotman)在1569年的著作《圣言的安慰》(Consolatio Sacris Litteris)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表示,爱尔兰条文和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语言只是反映了正统教派已经持有一段时间的观点,他以此开头:“世界是神在六天内创造的。” [40] 在这样清晰的肯定之后,他写道:
“[第一天,神创造了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混沌:]最后有了光。因此,它被算为第一天。然而,在接下来的五天中,他将那些物质分离开,并安排了它们。第二天,他将水分开……第三天,神创造了旱地的物质。然后在第四天,他创造了天上的空间,在其中安排了太阳、月亮和其他的星体,他量给它们各自在其固定方向上的光的量度,就是他在第一天所造的光,以便从它们的运行中,可以确定年、月、甚至天的时间。第五天仅仅……但到了第六天,第一次有行走[在地上]的野兽。”[41]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霍特曼(很难想象与加尔文、马特尔、穆斯古勒斯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认为这些天是连续的、普通的,并且按照我们今天数算正常天数的方式来数算。
在第一代改革宗神学家中,这些经典解释一直占主导地位,至少延续到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会的时代。这里列举的证词远非是选择性的,在日内瓦、普法尔茨(德国)、苏黎世、荷兰或英国,确实很难找到例外。在1540至1740年间肯定很难找到长日论、类比日或框架理论的传扬者。考虑到今天经常有人说改革家们和神学委员们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甚至与时俱进,这就令人称奇了,更不用说值得解释了。
欧洲大陆的改革宗神学家,1590-1690年
撒迦利亚·乌尔西努斯(Zacharias Ursinus)在对《海德堡教理问答》的评论中指出:“根据普遍的看法,从现在的基督1616年算起,距创世已有5534年。”[42] 他补充说,梅兰乔恩(Melancthon)估计这个年龄是5579年,路德估计是5576年,日内瓦的估计是5559年。如果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会主张漫长或不确定的创造时间,那么1616年的乌尔西努斯(更不用说其他改教家)在30年后就被彻底反驳了。乌尔西努斯继续说道:“这些计算在大位数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在小位数上有些出入。根据我们这个时代最博学的人所进行的这四个计算,综合考虑,就会发现世界是在不超过5559或5579年前由神创造的。因此,这个世界不是从永世就存在的,而是有一个开始的。” [43] 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s)采用了相同的宇宙年龄和年表,表明了他的立场。[44]
后来,乌尔西努斯对第四条诫命发表了评论:“以自己在第七天休息的榜样,他(神)可以最有效和最有约束力地劝勉人们来效仿他,在第七天放下他们在一周的其他六天习惯了的劳动。”[45]
约翰·迪奥达蒂(Diodati)是来自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的最著名的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在他的《对圣经的虔诚注释》(Pious Annotations Upon the Holy Bible,1643年)中,他多次表达了与加尔文相同的观点,并且在威斯敏斯特会议很久之后还拥护这一观点。迪奥达蒂在评论创世记1:3时说:“光起初很可能是固定在天的某个地方,它的转动形成了前三天,第四天光被限制在太阳或在所有其他恒星中,但是程度不一。”[46] 关于第4节,他指出,根据威斯敏斯特会议时日内瓦人的普遍看法,神“命令天空不断转动;并且当有光的半球[编辑,莱特富特(Lightfoot)也计算了半球效应以支持他的字面解释]在地球之上时,那应该是白天;当它在地下时,就是夜晚,这是昼夜连续更替的开始。” [47]
狄奥达蒂《对圣经的虔诚注释》在一个世纪里是最权威的著作之一, 解释在创世记第一章中“晚上”的含义为“那是夜晚”,就是按照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式,以日落为一天的开始,这与西方的时间惯例相反。狄奥达蒂继续说到,晚上的含义是“在天空的第一次运转中,只有上述事物被创造出来。” [48] 关于创世记2:2,狄奥达蒂(加尔文和贝扎的继承人)评论说:“他停止展示自己创造新生物的美德和能力,但并没有停止按自然的规律对它们的保护、维持和增长,并以自己的眷顾来引导它们。”[49] 狄奥达蒂进一步指出,神“在第七天结束了创造的工作…… 通过这样的休息,神就不会无限地继续创造,因此他也不会给他打算制造的留下任何不完美之处。”[50]
关于希伯来书11:3,狄奥达蒂写道:“也就是说,世界[参希伯来书1:2注,那里他将世界定义为‘一切暂时的事物,受制于时间的过程、分隔、和交替’] [是由圣言创造的]出于虚无,靠的是神独一的全能和意志。”[51] 关于罗马书4:17,狄奥达蒂解释说:“也就是说,他的话使之成为现实……就像他在万物的创造时,以及在基督复活的神迹中所做的那样——要有光,拉撒路出来,等等。”[52] 因此,通过将所有的创造归功于神的全能、意志以及他的话,他排除了创造是仅靠自然规律或主要依靠自然规律的观念。
1619年荷兰《多特会议法定全圣经注释》(Annotations upon the Whole Bible ordered by the Synod of Dordt)是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会和其他清教徒钦佩的解经书。在这里,我们发现关于创世记1:5的注释:“ [昼/夜]这两个词的含义是,黑夜和白天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然日,希伯来人的一日是从晚上开始,到第二天晚上,是二十四个小时。” 客观研究是否可以发现支持莱尔之后关于创世记第1章的观点的先例? 当现代人忽视这种强有力的见证时,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约翰内斯·波利安德(Johannes Polyander)在多特和威斯敏斯特两地都发表过著作,他清楚地表明,上述观点在他那个时代占据主导地位。1624年,保利安德捍卫该论点:“我们知道,世界的创造是从无到有,靠的只是神的美德和全能,正如圣经和使徒信经所确认的。”[53] 保利安德认为,圣经和信经都要求把创造理解为是靠神的命令,而不是其他的自然机制。他继续断言,这个世界是从无到有被创造的,神的全部创世之工是“在六天的时间里完成的,以彰显他极大的荣耀和智慧。”[54] 应该指出的是,波利安德在这里用的拉丁语(sex dierum spatio disposuit,“六天之内”)在语义上与加尔文和威斯敏斯特的用语非常相似,表明在当时该用语几乎得到了普遍赞同。
其他改教运动后的巨人也肯定了这一共识。约翰·奥西安德(Johan Osiander)确认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人类都是在六天之内受造的。[55] 另一位与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会同时代的荷兰人约翰·亨里希·海德格尔(Johann Henrici Heideggeri)也认可类似的结论。在他的《圣经列祖年表》(Chronologia Sacra Patriarchum)中,他的第一个条目是:“亚当是在秋天前后的创世第六天受造的,这一天对应于我们的十月的最后一天。” 该时间在他的“年表”中标为第一年,其他时间依次顺排。[56]
海德格尔还反复地指出,世界的创造始于秋天,并在其他地方指出,摩西的本意是将之作为元年。海德格尔对年表非常认真,甚至还讨论了如果10月31日是亚当受造的时候,就是第六个连续的、正常的日的早晨,那么10月26日可能就是创造的第一天。[57] 此外,改教运动的主流共识并没有像珀金斯和其他许多人那样回避创世的时间,而是明确地将之定为基督诞生前的3983年。海德格尔甚至提议亚当受造是在“我们的三点钟”。[58] 尽管海德格尔明白这样的年表可能只是一种启发性的传统,但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重要的是要指出,他和其他人把第六日的时辰视为真实的时间,就像我们现在的时间一样,而不是虚构的或误导性的文学手法。后来,海德格尔确认第六日被分为12个小时的光明和黑暗。[59] 他总是将时间标记视为真实的时间,一开始就问:“亚当是在一年中的什么时候受造的?”[60]
从加尔文到威斯敏斯特之后的50年间,没有任何有名望的改革宗神学家为现在的间隔论、长日论、类比日论或框架假说留下任何神学余地。更进一步,这些优秀的卫道士解决了现代基督徒认为如此难以解决的大多数疑问。他们对巴西流、安波罗修、约翰金口、兰巴德和其他人已经给出的回答非常熟悉,并一致认为“神话语的能力”是为受造物赋予生命的“唯一”能力。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神创世的神迹设定各种力、过程或比“自然日”更长的时间。他们的解释是基于神迹,而不是创造之后的维护。这些神学家中有许多人使用“在时间上”(in tempora)、或者指定白天和黑夜有12个小时、或者经常使用拉丁语时间的与格来表示这些是真实的而不是象征性的小时。他们并不像某些现代古老地球论的倡导者所说的那样模棱两可。他们都没有主张创造是很长的几段时间或创世的几天是不连贯的。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采用了同样的年表,并提供了自创世以来的年份,这只能符合字面的解经。
下面的研究回答了另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重要问题:英国的清教徒,例如埃姆斯(Ames)、珀金斯、莱特富特等人理解这个问题是否模棱两可或留有余地?现在关于这些人有大量的文本证据,历史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再次推翻了现代派的假设。
不列颠清教徒解经家
从各方面看,清教徒的巨人威廉·埃姆斯(William Ames,1576-1633)都可以视为改革宗正统的旗手。他生活在威斯敏斯特会议之前,否认了奥古斯丁的构想,对神学委员们起了主要影响,并为威斯敏斯特共识铺平了道路。但是由于约翰·麦克弗森(John Macpherson)的现代学术偏见,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埃姆斯为兼容进化论的宇宙学构想提供了依据。麦克弗森显然是凭空捏造证据,错误地宣称埃姆斯认为在创造日之间有很长的年代。[61] 不幸的是,这种错误的陈述常常广为流传,被人不加思考地接受,而没有去实际查考作者自己的原话。
对埃姆斯的仔细审查暴露了麦克弗森的历史修正主义。埃姆斯的主张与奥古斯丁相反,认为整个宇宙并不是同时(瞬间)被创造的;而是分部创造的,“每个部分依次受造,连续六天,有[正常的天与天之间的]间隔。” [62] 如果将埃姆斯理解为反对奥古斯丁/亚历山大学派的观点,即所有六天的创造都发生在一个瞬间,埃姆斯的主张只不过是重申了安波罗修的(传统)观点。他的话本身就与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们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一致,而不是反对他们。再者,只要埃姆斯不被普遍认为是主张几个漫长时期的创造(这也不是前面的文字证据所显示的观点),单靠麦克弗森的修正主义是不能证明埃姆斯站在深度时间这边的。
剑桥学者威廉·珀金斯(1555-1602)是个清教徒、辩论家和传道人。他的著作在英国清教运动的顶峰时期像加尔文的著作一样流行,他主张字面解释,与乌雪、莱特富特、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们、以及由他带领信主的著名的威廉·埃姆斯如出一辙。
珀金斯就创世之日这样评论说:“第六点触及世界的开始,就是五千到六千年之前。因为摩西已经精确地记下了从造世界到他自己时代的时间计算;而在他之后的先知们也勤恳地将这种计算延续到了基督的诞生……有人说从创世到基督诞生的年数是3929,如贝罗阿尔杜斯(Beroaldus);耶罗姆(Hierome)和比德(Bede)认为是3952年;路德和露西杜斯(Lucidus)认为是3960年;梅兰克顿(Melancton)在他的《纪事年表》(Chronicles)中认为是3963年,丰图斯(Functius)也一样;布林杰(Bullinger)和特雷默里乌斯(Tremelius)认为是3970左右;还有人认为约有4000年,如邦廷格斯(Buntingus)…… ”[63]
珀金斯反对奥古斯丁提出的瞬时创世,他坚持认为:“第七,有人可能会问神创造世界用了多少时间? 我回答说,神可以在一个瞬间创造出世界,以及其中的万物。但是他在六天之内开始并完成了整个工作。”[64] 关于神为何花了这么多天来创造,珀金斯认为: “用六天,是要教导我们他对所有受造之物拥有多么奇妙的权力和自由:因为在没有太阳、月亮、星辰的情况下,他创造了光;告诉我们,他把光赐给世界时,不受太阳、任何受造物或任何手段的束缚:因为光是在第一天造出来的,但太阳、月亮和星星却是到第四日才被造出来的。[65] 根据珀金斯的文字背景、年表和他的门徒对他的理解,珀金斯诚然不为现代的深度时间观点提供任何支持,而是肯定了年轻地球神创论观点的正统性。
在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之前不久的亨利·安斯沃思(Henry Ainsworth)也与当时的共识一致。在《摩西五经和诗篇注释》(Annotations on the Pentateuch and Psalms)中,提到创世记第一章,他写道:“从日落到日落24小时的天,以及更严格的从日出到日落12小时的天,如之前在第5节指出的,在诗篇104:19-23中展示了一种特殊用途。”[66] 关于创世记1:5,他说:“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67]
在乌雪之前,其他大多数人也以类似的方式定义创世的几天。沃彻斯特主教杰维斯·巴宾顿(Gervase Babington,1550-1610)评论创世记1:7时说,神创造“不是在一瞬间,而是在六天的时间里”,从而展示“六天的时间” 这个词组的早期使用是指实在的六天。[68] 后来,巴宾顿指出,神在“六天创造”之后的第七天安息了,[69] 绝对没有一点暗示那时有漫长的创造时期的观点。
威斯敏斯特会议之前还有一个安德鲁·威利特(Andrew Willet,1562-1621)。威利特在《创世记中的六天》(Hexapla in Genesis)中,讨论了世界是六天还是瞬间创造的。他认为,摩西的记载,必须按字面意思直白地接受,他说:“如果世界是瞬间创造的,那么六天创造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但是,奥古斯丁在别的地方却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世界不是一日之内创造的,而是为了……” [70] 这个资料显明,威斯敏斯特会议之前的一代人一致否认奥古斯丁的瞬时创造观。
威斯敏斯特会议的另一个同代人,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1580-1654),阿尔达的主教,参与写作了这些释经书。他后来(1655年)对那些注释的补充得到了乌雪和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托马斯·各特克(Thomas Gataker)的认可。在至少一位主要神学委员(各特克)的支持下,理查森在《创世记注释》(Annotations on Genesis)中写道,创世的几天是“自然的天,由24小时组成。”[71] 此外,他评论说:“晚上是夜的开始,早晨是昼的开始,晚上和早晨,被称为第一天,大概就是自然24小时的一天。” 后来,关于创世记1:5,理查森写道,这一天的时间是按犹太人的正常算法,“因为24小时的自然日的开始是来自创世,关键点是,它必须包含二十四小时。”
温彻斯特主教兰斯洛特·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断言,创世的天应该按如下计算:“从日落到日落是一天。” [72] 后来,安德鲁斯肯定说:“因此,我们说一天有二十四小时 …… 这一天本身就是一天,就像其他六天一样。” [73] 安德鲁斯引用巴西流的话评论道,“yôm”这个词(创世记1:5中的“日”)“就是自然用法的意思,我们应该尊重一天是二十四小时。第一天是后面几天的范例。” [74]
后来反对奥古斯丁的错误立场的神学家们继续坚持这唯一的传统,直到18世纪中叶。关于这种经典的创世观的普遍性的唯一争论在于它是何时开始受到挑战或侵蚀的。似乎无可争议的是,改革宗的释经家们在这一点上相当一致地拒绝了奥古斯丁的思想,而追随彼得·伦巴第和阿奎那。在宗教改革之前、之中和之后,他们绝对保持一个共识,将创世记的“天”解释为正常的一天。一些当代的古老地球倡导者提议说,威斯敏斯特之前的主要人物可能不止“只有一个声音”。但是,至少在正统的改革宗学者的著述中,这种宣称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威斯敏斯特会议的总结
出乎意料的是,有些人争辩说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们在一日的长短及相关问题上留下了不可知论、淡漠论、或多元论的遗产。但是,为了让人认真地对待这些指控,批评家们必须提供来自这些神学委员本人的确凿文件,证明他们预示了现代古老地球支持者的宽广和兼容。[75] 我们证明,这些神学委员们在17世纪中期对一日的长短其实有固定的看法;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后期,极少有例外。
威斯敏斯特信条有意识地用文字确立了一个真理主张:“在六天之内”。该词组在写下时具有特定的含义,并且其含义仍然是可验证的和明确的。因此,那些在过去150年中声称“在六天之内”的宣告词其实可能意味着长达140亿年的人,表明了自己并没有在相关的原始资料中用心研究。
我们在对该问题进行大量研究之后,并没发现有可靠的证据显示这些神学委员们允许非字面的天或某种类型的框架假设。[76] 相反,至少有23位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有的参与会议,有的受命服侍,有的为大会做记录)直接或间接作证,他们相信有六个24小时的创造日(与奥古斯丁的立场相反),而创世周发生在短短几千年前。并不是所有的神学委员都在这一点上留下了证词,但是我的研究发现没有人与正常日的观点相矛盾。支持古老地球的人有责任提供书面证据,表明教会那时对创世记第1-11章的理解是模棱两可的。
威斯敏斯特会议之后一百年的改革宗神学家们,1640-1740
威斯敏斯特会议之后不久,约翰·欧文(John Owen)、托马斯·文森特(Thomas Vincent)、托马斯·曼顿(Thomas Manton)、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弗朗西斯·图雷汀(Francis Turretin)和其他许多人确认其前人的观点,并否定奥古斯丁的观点。托马斯·怀里(Thomas Wylie)的《教理问答》(Catechism,约1640年)也以这种主张来反驳奥古斯丁:“问:主在创造工作中用了几天?答:虽然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在一瞬间就结束了,但主用了六天的时间。” [77]
图雷汀于1679年提到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并否定了他,而与乌雪站在一边:“摩西所写的神圣历史也没有覆盖六千多年。希腊历史几乎不超过两千年。”[78] 图雷汀甚至赞扬乌雪和其他人指出创世发生在秋天而不是春天。[79]
托马斯·波士顿(Thomas Boston)发表著作的时间比图雷汀稍晚一点,但在这一点上继续了改革宗对奥古斯丁主义的批判(再次使用“六天之内”的字眼)。波士顿写道:
“我们的下一项任务是展示创造世界用了多长时间。从摩西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在六天的时间内完成的,而不是像奥古斯丁所说那样瞬间完成的。对神来说,瞬间完成和六天完成一样容易。但是他采取了这种方法,以便创世之工表现出的智慧、良善和力量显明在我们眼前,并激起我们对这些工作的特别思考,他为了纪念这些工作而把第七天[ 24小时]指定为安息日。”[80]
后来,波士顿重申了与奥古斯丁和约翰·科莱特(John Colet)的对立,“尽管神并没有在一瞬间造出万有,” 他仍然“在这六天内创造了天使。”[81] 他接着列举了每天所做的事情,很肯定地没有把这些天想象为超过24小时。波士顿与乌雪完全一致,响应当时的共识:“世界被创造的季节很可能是秋天,这通常是万物达成完美的季节。”[82] 在威斯敏特会议之前和之后,在这样的年表问题上,乌雪而不是奥古斯丁主导着17世纪的神学界。
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637-1708)是持守加尔文信条的主教和虔诚的高级教士。他生活在威斯敏特会议之后不久,是一位著名的传道人,在英国国教中复兴了加尔文教派的虔诚。他著有一本广为流传的著作《关于宗教的私人思考》(Private Thoughts on Religion)。关于第一天,他说:“所以最初造的光具有相同的运动方式,它照耀在在哪里,那里就是白天,在所有的其他地方就是黑夜,直到光再次来临——这就像现在太阳在二十四小时内的运动一样;这样,晚上(当光落下时)和早晨(当光再次升起时)就是自然的第一天,与我们现在的天长度相同。”[83]
托马斯·里奇利(Thomas Ridgeley,1667-1734)是《威斯敏大要理问答》最全面的注释者,他提出了几个要点。他在题为“创世六日的工作”的段落中论述了神是如何(藉着神大能的话)以及为什么(为了他的荣耀)而创造的。[84] 在这里,他解释了每天所创造的东西,以及天使和光如何在第一天被创造,虽然直到第四天光 “才被收集到太阳和恒星里”。[85]
里奇利讨论了奥古斯丁的瞬时创造理论,并明确表达了他的歧议。他的书中甚至有一个标题为“受造界并非永存”的部分,他说:“圣经里有世界持续到现在的时间,不超过五到六千年。”[86] 与参加威斯敏斯特会议的苏格兰成员罗伯特·贝利(Robert Baillie)一样,里奇利也考查了“万物是在一年中的什么时间或季节被造的?”并得出结论是在秋天。[87]
德瑞主教以西结·霍普金斯(Ezekiel Hopkins, Bishop of Derry,1633-1689)谈到了安息日是何时设立的。他写道:
“……他就在创造后的第七天休息;因此,神就使第七日那一天成为圣日,并将其作为随后所有安息日的开始。这样你就可以明白安息日只比人的创造晚一天,是在人正直清纯的状态下为他设立的……而且,尽管我们随后看不到提及安息日的经文,直到摩西将以色列百姓带入旷野,大约在创世后的2450年……”[88]
之前,霍普金斯计算了十诫颁布的实际时间:“根据对年代的最佳计算,时间是创世后的大约2460年……”[89] 他不仅为地球的年龄论证,还明确表示安息日“比人的创造晚一天”,这清楚地表明他将创世的每一天视为二十四小时。[90]
弗朗西斯·罗伯茨(Francis Roberts,1609-1675)是罗伯特·贝利的密友。每当贝利需要引起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时,罗伯茨竭力为他效劳。罗伯茨本人就创世记载写了一些东西。“这里描述了世界的创造……根据神在六个不同工作日的有序进程。”[91] 而且,与同时代的所有其他神学家一样,他坚定地将创世记中所记载的全部历史年代从创世之日算起:“创世记的历史是明显的2368年的连续的历史。”[92]
乔治·休斯(George Hughes,1603-1667)在对创世记的评论中写道:“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天的构成,原文是一日。但请首先阅读:晚上和早晨被合在一起来代表[93]所有黑暗和所有光明,形成一个自然日。光明的时间,或说十二个小时的部分,是民间的日。”[94]
约翰·确普(John Trapp,1601-1669)是一位受人欢迎且学识渊博的圣经注释家,于1646年从神学委员会获得格洛斯特郡和沃里克郡韦尔弗罗德的教区长职位。在他对摩西五经的注释中,确普说:“后来主确实为之赋形…… 在三天之内奠定了世界的各部分,在另三天中为之装饰。[95] 在他的《神学讲义:真正的宝藏》(Theologia Theologiae: The True Treasure)书中,他把以斯拉书的时间定在“创世后大约三千六百年,在世界现存的世事记之前”,这表示创世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96] 这与1540年至1640年间学者们确定人物年代的方式相似。
卫斯理和19世纪早期的圣经注释
先前讨论的人是改革宗圣经学者。尽管如此,亚美尼亚主义领导人约翰·卫斯理(1701-1791)对创世记的看法与他的改革宗弟兄们相同。[97] 他清楚地意识到科学的实用好处,并撰写了两本书来普及医学和电力方面的有用知识。但是他对理论科学保持警惕,因为它有可能带领人们走向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在他的两卷《创造中神的智慧概览》(Survey of the Wisdom of God in the Creation,1763)中,他呈现了传统的从设计证明神存在的论点,这些论点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英国非常流行。[98]
卫斯理没有花很多的笔墨在创世或洪水上,但他在这本书中说他相信各种岩石地层“无疑是挪亚时代的大洪水所形成的”。他认为创世记与其他圣经书卷一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错误。” [99] 关于地球的年龄,他写道:“世界上只有圣经这一本书告诉我们上帝自创世以来四千年间在人类中的一整套计划。” [100] 在数篇公开发表的讲道中,他反复强调原始的创造是完美的,没有任何道德或肉体上的邪恶(例如地震、火山、杂草和动物死亡),两者都是在人类犯罪之后进入世界的。[101]
19世纪初,当亿万年的思想深入地质学中时,对创世记的字面解释继续在教会中占主导地位。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托马斯·霍恩(Thomas H. Horne,1780-1862)的工作,他是英格兰教会的神职人员,然而在他的大部分工作生涯中,他也在大英博物馆的印刷书籍部门担任助理馆员。他没有写过一本圣经注释,但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圣经学者之一。
在他众多的出版物中,最伟大的著作是《圣经批判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Study of the Holy Scriptures)。他经过17年的研究,于1818年首次出版该著作,分三卷(1700页)。由于在自己的圣经研究中找不到足够的资源,霍恩阅读并且在许多时候购买了最杰出的圣经评论家的著作,包括英国和外国的评论家。[102] 霍恩的著作经过不断地修订和扩展,到1846年的第9版增为五卷,此后在英国又发行了两个修订版,那些年间在美国也发行了许多版本。尽管其规模大,成本高,但这些版本在英国的销量超过15000册,在美国也发行了数千册。[103] 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了代表所有宗派(包括高级教会和福音派英格兰教会)的杂志的好评,成为大英帝国所有讲英语的新教学院和大学中有关圣经研究的主要教科书。[104] 为普通人设计的单卷精简版《圣经研究简介》(A Compendiou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Bible)于1827年首版,最终于1862年达到了第十版。
跟当时的大多数英国基督徒一样,霍恩坚定地相信圣经是文字上的、整体上的、无误的默示。在谈到欧洲大陆圣经批评家的论点时,霍恩为摩西作为摩西五经的作者和创世记的字面历史性,特别是前三章,提出了激烈的辩护,指出创世记“叙述了所有受造物的真实起源和历史,与外邦所乐道的错误观念相对立。” [105] 霍恩还回应了反对全球性挪亚洪水的意见。他认为,化石、人口规模、艺术和科学的晚近发明和进步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民族的洪水传说都证实了这一点。[106] 一直到1856年版的《导论》,(由于受古老地球地质理论的影响)霍恩才放弃了这一立场,转而采用间隔论和局部洪水理论。[107]
在19世纪初期的英语世界中,有很多圣经注释可用,绝大多数都遵循传统观点,甚至倡导乌雪关于以公元前4004年作为创世时间的观点。[108] 其中最流行的注释值得简要地评论。他们全都坚持年轻地球创造论的观点。
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1747-1821)是英格兰教会的神职人员,与约翰·牛顿(John Newton)成为朋友,并最终接替约翰·牛顿成为白金汉郡奥尔尼教区的牧师。他的圣经注释最初写于1788年至1792年间。在英国,斯科特在世时出了四版,其后至少又出了两版,在美国出了八版,总计超过37000册(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销售记录),也被翻译成威尔士语和瑞典语。根据詹姆斯·史蒂芬斯(James Stephens)爵士的说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最伟大的神学作品。”[109]
著名的英格兰教会神学家和创建伦敦国王学院的主要推动者,乔治·德·奥利(George D’Oyly,1778-1846)和英格兰教会教区长、后来升为主教的理查德·曼特(Richard Mant,1776-1848)是两位高级教士。他们在1817年为中产阶级出版了一本解经书,作为托马斯·斯科特和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最流行的福音派书籍的替代品。他们的脚注中引用了160位作者。第二版于1823年发行,而1818年的小型纸质版更是当时所有的解经书中最便宜的。[110]
亚当·克拉克(Adam Clarke,1762-1832)是循道会的传道人,是约翰·卫斯理的亲密朋友,也是当时他的教派中最伟大的学者。他在1782年至1808年间在伦敦及其周围的宣道点之间步行了7000英里,作了6615章内容各不相同的讲道,还掌握了古希腊罗马经典和早期教父及东方作家的著作,并为此学习了希伯来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梵语和其他东方语言。自然科学也是他喜欢的学科。在那些年间,他成为了古文物学会(1813)、爱尔兰皇家学院(1821)、地质学会(1823)、皇家亚洲学会(1823)和其他学会的会员。他最伟大的作品是他的圣经注释,于1810年至1826年间写成,并多次发行修订版,直到1874年。[111]
约翰·吉尔博士(John Gill,1697-1771)是一位浸信会牧师兼圣经学者。他的巨著《圣经解析》(Exposi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是在1746年至1766年之间完成的。根据霍恩的说法,他在犹太拉比文学上无人可以匹敌,但是他经常过分地灵意解经,[112] 这使他对创世记的字面解释更有意义。另一位浸信会神学家是安德鲁·富勒(Andrew Fuller,1754-1815)。富勒帮助建立并指导了浸信会宣教协会。他是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的牧师,影响后者成为浸信会宣教协会的第一位宣教士。富勒的两卷《创世记解析》(Expository Discourses on the Book of Genesis)发表于1806年。[113] 马太·亨利(1662-1714)是一位非国教神学家,他的圣经注释在18世纪和19世纪广为人知并受到珍视。[114]
所有这些圣经注释家都持守字面六天的创造,认为创造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4000年,并相信挪亚时代的全球性洪灾。直到1845年左右,在莱尔解释岩石的均变论框架已经完全占据了地质学之后,英语的圣经注释才放弃上述观点。[115]由于高等圣经批判对欧洲大陆的影响,年轻地球的观点在欧洲大陆被遗弃得更早。
尽管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广泛使用的圣经注释维护了年轻地球观点,但这并不反映所有福音派人士和高级教会人士的观点,莫腾森(Mortenson)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古老地球地质学的起源。除了莫腾森要讨论的著名的古老地球支持者外,高级教会杂志《英国评论家》(British Critic)和《基督教纪念者》(Christian Remembrancer)以及福音派杂志《基督教观察家》(Christian Observer)的编辑们也普遍接受了古老地球地质学理论,不过他们在如何将古老地球与圣经协调的问题上并没有坚定的立场(包括关于创世记第1章的长日论、间隔论,及局部或平静的挪亚洪水论)。由于新的地质学理论的影响,所有这些基督徒都对创世记采用了古老地球的解释,但是他们都宣称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是无误的,且在历史上是可靠的。因此,对于这些福音派和高级教会的古老地球拥护者而言,问题不在于圣经的本质,而是圣经的正确解释以及科学在决定解经中的角色。
结论
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了从路德到莱尔的地质均变论胜利之前的主要基督教思想家(与从使徒到路德的基督教思想家一样)将创世记第1-11章视为直截了当的字面历史。在教会中,捍卫现代古老地球支持者所推崇的长日论、间隔论、类比日或框架观点的扎实的解经者在哪里呢?
正如莫滕森在下一章中所要解释的那样,在19世纪初,教会并非由于更审慎的解经学要求而改变其对创世、洪水和地球年龄的看法,而是因为古老地球地质学理论被当成已被证明的事实,并强加在创世记的经文上。
到19世纪末,神学格局发生了变化,从而使沃菲尔德(Warfield)、谢德(Shedd)和其他人可以假装加尔文和前辈们实际上已经预见了许多现代的进化思想。有了这些中坚力量登上该领域的现代派火车——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对新派思想的某些领域持续排斥——就为20世纪逐步削弱福音派的传统提供了掩护。很快,这一传统便朝着在释经上与怀疑论的科学机构保持一致的方向发展。结果是,一些新的解经范式得到了认可,许多优秀的福音派人士就很少听到经典的观点,因为他们只受到单方面论点的教导。
本·斯蒂勒(Ben Stiller)出演了2004年票房大满贯《躲避球》(Dodgeball)。在那部电影中,就像在躲避球游戏中一样,需要进行各种扭曲以避免被打出局。有时,扭曲接近于变态。在这项运动中,一个人可能会太努力地躲避球,以至于他可能越过另一条线,击中另一名球员或在其他方面犯规。现在看来,1800年以后的释经历史很像这场游戏:它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理论上的折腾或冲击。在此过程中,这些不断发展以适应当时理论的观点变得如此扭曲或变异,以至于历史性的观点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过,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避免这种做法。[116]
创造论学说也可以为现代基督徒提供一面镜子,它可以用来反映我们的本相。除非我们有这样的镜子,否则我们通常看不到我们的本相。我们喜欢告诉自己,我们没有被世俗的理论所污染,但是这个问题的历史,尤其是在福音派人士中,似乎在讲相反的故事:与属世哲学的日益融合。
此外,该话题对于解经学、神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测验。当某个人在该问题上与古人的共识不同时,他就要对其中的差异进行辩解。当我们这样做时,发现我们被迫采用或接受的一些方法论原则,是我们在解释其他圣经教导时会迅速抛弃的。我们当然不会坐等科学来允许我们相信耶稣的道成肉身或复活,对吧?那为什么在创世的教导上我们要这样做呢?如果我们开始让我们的神学和信条得到现代主义的认可,我们要到哪里才会停下来呢?
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如此急于放弃其丰富的语法历史遗产以赢得雅典的尊敬呢?简单地保持一以贯之的神学方法并继续遵守我们的前辈经过时间考验的解经法,难道不是更明智的行动方针吗?
亚伯拉罕·林肯的建议是绝对正确的:“当您在生活中迷失时,请像在森林中迷路一样做。回追你的脚步。”如果我们通过这篇简短的回顾重新调整心意,这可能会有助于许多基督徒迷途知返。也许那些没有受到进化论偏见影响的敬虔的前辈对创世记的解释比大多数现代基督教学者更好吧?
[1] Walter Kaiser等, Hard Sayings of the Bible (Downers Grove, IL: IVPress, 1996), p.104. 又见于 Walter Kaiser, Towar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78), p. 75.
[2] John A. McIntyre, The Misuse of Scienc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93), p. 24.
[3]这些内容的有些部分曾经发表于David W. Hall, Holding Fast to Creation (Powder Springs, GA: The Covenant Foundation, 2001, 2nd ed.). 又见 David W. Hall, “The Evolution of Mythology: Classic Creation Survives as the Fittest Among Its Critics and Revisers,” in Joseph A. Pipa Jr. and David W. Hall, eds., Did God Create in Six Days? (White Hall, WV: Tolle Lege Press, 2005), p. 265–301.
[4] Andrew Dickson White, 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896), p. 49.
[5] 同上,第 60页。
[6] 参例如: Martin Luther, Luther’s Works, vol. 17 (St. Louis, MO: Concordia, 1972), p. 29, 118
[7] 请参本书中余理斐(Thane Ury)的章节。
[8] Robert Letham, “ ‘In the Space of Six Days’: The Days of Creation from Origen to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vol. 61:2 (Fall 1999): p. 149–174. 也参 Pipa and Hall, Did God Create in Six Days?, p. 280,关于路德的脚注28.
[9] The Works of Hugh Latimer, I:20.
[10] 同上,I:52。
[11] Robert C. Bishop, “Science and Theology: A Methodological Comparison” 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vol. v, no. 1/2 (1993): p. 155.
[12] Howard Van Till, The Fourth Day (Grand Rapids, MI, MI: Eerdmans, 1986).
[13] John Calvin,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J. T. McNeill, ed. (Philadelphia, PA: Westminster Press, 1960), 1.13.7.
[14] 同上,1.13.14。
[15] 同上,1.14.2。
[16] 同上。
[17] 同上,1.15.5。
[18] 同上,1.14.20。
[19] 同上,1.14.22。
[20] 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Genesis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79), 1:70.
[21] 同上,p.90。
[22] 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79), p. 264–265.
[23] 同上。
[24] John Calvin, Genesis, translated by John King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2 reprint), p. 78. 他对1:16作了相似的注释(第86-87页)。
[25] 有一个流行的传说,说奥古斯丁先发制人地预见了均变论。穆克(Mook)在本书第一章里指出,奥古斯丁对创造日长度的困惑是由于他的拉丁语译本有错而他自己又不懂希伯来语。但是尽管奥古斯丁确实没有支持24小时的日,他实际上是朝相反的方向而去,把创世的六日当成一瞬间。所以休·罗斯(Hugh Ross)和其他古老地球支持者来跪拜在奥古斯丁脚前,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他们因为误解了奥古斯丁的观点而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改教运动之后的“争论”不是在深度时间与字面的日之间,而是在纳秒与字面的日之间。
[26] Calvin, Genesis, p. 76(第一点), 81, (第二点), 83 (第三点), 111 (第四点), 250, 272, and 281 (第五点), and 231 and 313 (第六点).
[27] Theodore de Beze, Cours Sur les Epitres aux Romains et aux Hebreaux (1564-1566) in Travaux d’Humanism et Renaissance (Geneva: Librarie Droz, 1988), vol. 226, p. 311. 清教徒传道人William Perkins 在他长篇的Commentary on Hebrews 11 (Boston, MA: Pilgrim Press, 1992 reprint) 中也类似地教导11:3.
[28] 这一段落的部分是引自我与Mark Herzer 和 Wesley Baker所著文章 “History Answering Present Objections: Exegesis of the Days of Creation a Century Before and After Westminster, 1540–1740,” 发表于我的书 Holding Fast to Creation (Powder Springs, GA: The Covenant Foundation, Second edition © 2001)中.
[29] 参 David W. Hall, “What Was the View of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Divines on Creation Days?” in Pipa and Hall, Did God Create in Six Days?, p. 41–52.
[30] Annotations from the Geneva Bible (1562), p. 4.
[31] Wolfgang Musculus, In Genesim Moses Commentarii Plenissimi (Geneva, 1554), p. 9.
[32] 穆斯古勒斯的拉丁短语字面的意思是 “不是从时间开始的点算起,而是从标定时间的点算起。” 如此,他加强了希伯来人把晚上当成一天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的时间计算方法。
[33] 同上,第13页。
[34] 同上,第26页。
[35] 同上,第29页。
[36] Peter Martyr, “The Propositions of D. Peter Martyr, disputed openlie in the Common Schooles at Strasbourgh,” contained in Peter Martyr’s Works (London, 1558, trans. by Anthony Marten, reprint of 1543 original), p. 144.
[37] 同上,第144页。
[38] Ussher, Summe and Substance (London, 1647), p. 94.
[39] Martyr, “The Propositions of D. Peter Martyr . . . ,” p. 144.
[40] Francois Hotman, Consolatio Sacris Litteris (Geneva, 1569), p. 1.
[41] 同上。
[42] Zacharias Ursinus, Commentary to the Heidelberg Confession, (Columbus: Scott and Bascom Printers, 1852, reprint of 1616 original).
[43] 同上,第1450页,强调是外加的。
[44] William Perkins, Works, I:143–4.
[45] Ursinus, Commentary to the Heidelberg Confession, p. 531。
[46] John Diodati. Pious Annotations Upon the Holy Bible (London, 1643).
[47] 同上。
[48] 同上。
[49] 同上。
[50] 同上。
[51] 同上。
[52] 同上。
[53] 在Herman Bavinck, ed., Synopsis Purioris Theologiae (1624, reprint 1881), p. 83中引用.
[54] 同上。
[55] Johan Osiander, Orthodox Animadversions (Tubingen, 1693), p. 301 (Locus V, xiii).
[56] Johann Henrici Heideggeri, Historia Sacra Patriarchum, Exercitationes Selectae (1668; reprint Tigurinie, 1729), Part III, p. 547.
[57] Johann Henrici Heideggeri, Exercitu Quarta, p. xv, 84.
[58] 同上。
[59] 同上。
[60] 同上。
[61] 对这个问题更完整的分析,请参David W. Hall, “The Evolution of Mythology: Classic Creation Survives as the Fittest Among its Critics and Revisers,” in Pipa and Hall, Did God Create in Six Days? p. 285–287.
[62] William Ames, The Marrow of Theology (Boston, MA: Pilgrim Press, 1968), p.102.我发表在网上的版本附有更多的参考资料: http://home.comcast. net/~webpages54/ap/hallcreation.html
[63] William Perkins, An Exposition of the Creede, I:143. 这证实引用的所有作者都字面地理解创世的几日。
[64] 同上,I:143.
[65] 同上,I:143.
[66] Henry Ainsworth, Annotations on the Pentateuch and Psalms (Soli Deo Gloria, 1997 reprint), p. 6.
[67] 同上。
[68] The Workes of Gervase Babington (London: 1622), p. 6.
[69] 同上,第6页。
[70] Andrew Wilett, Hexapla in Genesis (London: 1632).
[71] John Richardson, Annotations on Genesis (London: 1655).
[72] Lancelot Andrewes, Lectures Preached in St. Paul’s Church (London: 1657), p. 661.
[73] 同上,第662页。
[74] 同上,第663页。
[75] 关于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的原意,有更多的资料证据,参 David W. Hall, “What Was the View of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Divines on Creation Days?” in Pipa & Hall, Did God Create in Six Days? p. 41–52.
[76] 许多位威斯敏斯特神学委员没有留下对这个课题的书面评论,但我没有找到一个反对平常日的观点。我最初的调研找到11个神学委员解释他们在《威斯敏斯特信条》 (第4章)和教义问答里用的“六日之内”的意思。为回应对我的发现提出的挑战,进一步的调研找到了25位。也参我所著Holding Fast to Creation, 及 Pipa and Hall, Did God Create in Six Days?, p. 41–52.
[77] Thomas Wylie, Catechism (London, 1644), p. 244.
[78] Francis Turretin, Institutes of Elenctic Theology, 3 vol.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92, repint of 1679–1685 original and edited by James T. Dennison), I:438.
[79] 同上,p.442,
[80]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omas Boston (Wheaton, IL: Richard Owen Roberts, 1980 reprint), p. 173.
[81] 同上。
[82] 同上,第174页。
[83] The Works of the Right Rev. William Beveridge, D.D., 9 Vols. (James Duncan and G. & W.B. Whittaker, 1824), III: 482.
[84] Thomas Ridgeley, Commentary on the Larger Catechism, 2 vols. (Edmonton, AB Canada: Still Waters Revival Books, [1855] 1993), 1:331–336.
[85] 同上,1:333.
[86] 同上, 1:328. 里奇利(Ridgeley)甚至不同意奥古斯丁稍微更早一点的创世时间,他把这归咎于奥古斯丁依赖七十士译本。
[87] 同上,1:336
[88] The Works of Ezekiel Hopkins, 3 vols (Soli Deo Gloria: 1995), 1:366–367.
[89] 同上,1:237.
[90] 同上。
[91] Francis Roberts, Clavis Bibliorum (London: George Calvert, 1665), p. 7.
[92] 同上,第6页。
[93] synecdoche 是一个文学术语,意思是用部分代表整体,或反过来用整体代表部分。诗篇 24:4 说到要手洁心清,这代表全人。
[94] George Hughes, An Analytical Exposition of the Whole First Book of Moses, called Genesis (London: 1672), in loc.
[95] John Trapp, A Commentary or Exposition Upon the Books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5 Vols. (London: Thomas Newberry, 1657), I:3.
[96] John Trapp, Theologia Theologiae: The True Treasure, vol. 4:683.
[97] 我感谢泰瑞·莫藤森博士在这些段落中做的研究和帮助。
[98] John Dillenberger, Protestant Thought and Natural Science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p. 156–58.
[99] John Wesley, Survey of the Wisdom of God in the Creation, 2 vol. (Bristol, 1763), II:22, p. 227. On the global Flood, see also his sermon on original sin in The Works of the Rev. John Wesley, 14 vol. (London, 1829-31), IV:54–65.
[100] Wesley, Survey of the Wisdom of God in the Creation, II:227.
[101] John Wesley, Works of John Wesley, IV:206–215 (“God’s Approbation of His Works), IV:215–224 (“On the Fall of Man”), VII:386–399 (“The Cause and Cure of Earth-quakes”), IX:191–464 (“The Doctrine of Original Sin, according to Scripture, Reason and Experience”, especially pages 196–197).
[102] T.H. Horn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Study and Knowledge of the Holy Scriptures (London, 1818), I:3
[103] S. Austin Allibone,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3 Vol. (London, 1877), I:890.
[104]同上, I:889; “Horne, Thomas H.,”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22 Vo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vol. 9, 1257–1258. 节选的评语出现在T.H. Horne, A Compendiou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Bible (1827, second edition) 的序言中,包括以下的杂志: Christian Remembrancer (英格兰高级教会), Evangelical Magazine (非国教), Congregational Magazine, Home Missionary Magazine, Wesleyan Methodist Magazine, and Gentlemen’s Magazine.
[105] T.H. Horn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Study and Knowledge of the Holy Scriptures (1818), II:18–38.
[106] 同上, I:485–490, II:37.
[107] 同上 (1856), I:583–590. 他表示William Buckland 和 John Pye Smith 是使他改变想法的两位主要影响者。
[108] 对霍恩(Horne)的著作和19世纪早期使用的圣经注释更多的论述,参Terry Mortenson,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The Church’s Catastrophic Mistake on Geology — Before Darwin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2004), p. 40–47.
[109] “Scott, Thomas,”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 17, 1011–1013; William Symington, “Introduction,” in Thomas Scott, The Holy Bible with explanatory notes by T. Scott (1841), p. xx.
[110] T.H. Horn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Study and Knowledge of the Holy Scriptures (1818), II: Appendix, p. 31; John Overton, The English Churc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00–1833 (London, 1894), p. 178.
[111] “Clarke, Adam,”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 4, 413–414; J.B.B. Clarke, An Account of the Infancy, Religious and Literary Life of Adam Clarke (London, 1833), II:313, 350, 402; III:35–36, 213, 472.
[112] “Gill, Joh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 7, 1234; T.H. Horn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Study and Knowledge of the Holy Scriptures (1818), II: Appendix, p. 27. Adam Clarke said much the same about Gill in his The Holy Bible with Commentary (London, 1836), I:9.
[113] “Fuller, Andrew,”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 7, p. 749–750.
[114] “Henry, Matthew,”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 9.
[115] Nigel M. de S. Cameron, Evolution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Exeter, UK: Paternoster Press, 1983), p. 72–83.
[116] 有的神学家最近不但不质疑达尔文,反而说教会需要为拒绝达尔文的理论而向达尔文道歉。参 Rev. Dr. Malcolm Brown (Director of Mission and Public Affairs for the Church of England), “Good Religion Needs Good Science,” www.cofe.anglican.org/darwin/malcolmbrown. html, accessed Sept. 16,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