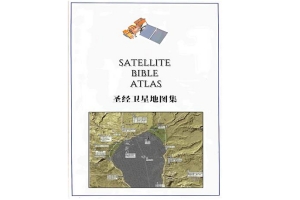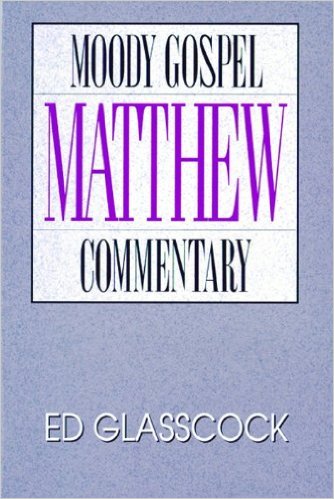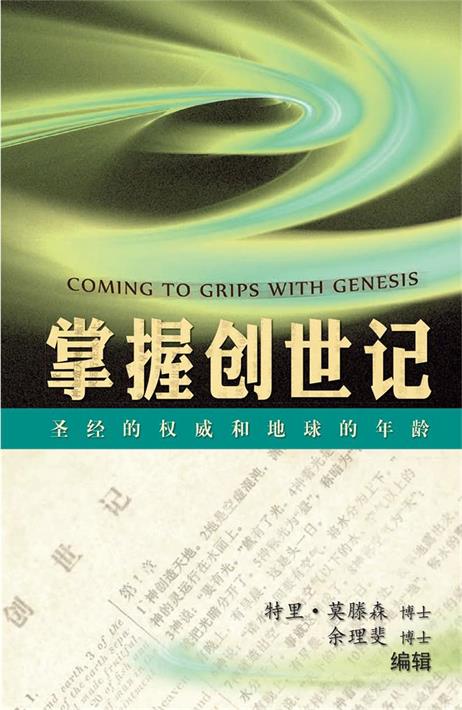
第十四章:路德、加尔文、卫斯理谈自然恶之起源:重拾遗忘的纲领,捍卫“甚好”的创造
余理斐(Thane Hutcherson Ury)
2008年夏天,我到中国四川旅行。震撼全省的大地震之后的余震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当然,与地震之后中国所经历的恐慌冲击相比,我的紧张不足挂齿。据报道,中国有8万多人在“5.12”大地震中丧命。死亡本就不幸,大规模伤亡更是如此。我的房东已经麻木了,他数不清自己失去了多少朋友。两位医生告诉我,死亡场面怵目惊心,不堪回首,而且后来尸体发出的恶臭对救援人员也造成了破坏性影响。面对这样的灾难,我们受重创的灵魂有时只能以麻木、哭号、或向天挥拳来回应。与实际行动相比,言语显得苍白无力。这点从中国人表达他们悲痛的方式就可以明了:地震整整一周后,我们在电视机里看到摄像头扫过人山人海,拍到的是全国人民低头集体默哀三分钟的场景。此举若非出于惊悚,便是表达对巨大死亡人数的悲痛和一致的声援。
对于亚洲来说如此损失并非新鲜。1556年发生于陕西的大地震夺走了83万条生命。[1] 近来在缅甸,强热带风暴纳尔吉斯致使13万条生命陨落。谁又能忘记2004年的海啸,使23万人成为受害者?而幸存者的残疾、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大灾后的疾病、动物的死亡、大规模的建筑结构破坏和经济的动荡更是雪上加霜。如何解释不断被类似的灾难戳伤的地球历史呢?更尖锐一些地讲,鉴于这样的惨况,我们何以能声称上帝确实存在?更别提他是良善和慈爱的了。
无论是伊拉克婴儿的脑瘤、被艾滋病困扰的尼日利亚村庄,还是泰国的海啸,都会引出自然之恶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彻底地跨越了文化、时间和信仰。无论是学者还是外行、无论是信徒还是讥诮者,大家都在问:“若有上帝,何以存在诸多的邪恶?” 对这个挑衅性的问题的解答在各种极端之间摇摆。一些无神论者将自然恶作为抵挡有神论的头条证据,甚至一些有神论者也提出了与教会先贤和当初的宗教改革家截然不同的论调,大胆地推出重新解读邪恶、上帝的良善和“甚好”的内涵的各种说法。
尝试回答有关邪恶问题的学问称为“神义论”。[2] 基督教神义论致力于解决以下难题:一个良善、全能的上帝何以与各种形式的邪恶、痛苦和死亡共存,容忍之甚至触发之?无论对于道德恶还是自然恶,有思想的人都想知道答案。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s)确信这个问题“是有神论者所面临的最严肃的智力难题。”[3] 如果他的话是正确的,那么福音派人士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深刻探讨这一问题。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为此难题冥思苦想直至得其要领,更别提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了。沉默的原因要么是由于没有将其视为问题,要么是思想堕怠或潜意识里认为神义论是“人类所有智力活动中最雄心勃勃、并且似乎注定会失败的理论。”[4] 卡蓬(Capon)适时地警告说这一问题是 “为坚韧的人而准备的”,[5] 布伦纳(Brunner)则从受造物(人)想要捍卫造物主这一点中看到了人隐含的傲慢。[6] 虽然如此,彼得前书3:15不允许逃避这类问题,基督徒必须捍卫真理。
基督教神义论的核心问题
所有的宗教都包含某种神义论,尽管其说法截然不同。印度教用恶报来解释邪恶;泛神论者认为邪恶是人的幻觉;佛教徒认为邪恶是一切存在的必然产物。在西方,有限神论者试图通过限制神的能力来为神开脱,正如开放神论者低估神的预知力一样。尽管这些方法可能都能自圆其说,但若用以安慰911事件的废墟上或四川大地震之后的人类状况,基本都是清汤寡水。然而,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基督教史观提供了一个风险更大的神义论,因而受到了更多的审视。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先列出三个关键的神义论公理:(1)基督信仰中三位一体的神是至善的;[7](2)他的能力没有限度;(3)邪恶存在。肯定其中任何一个或两个命题都不会造成任何问题。然而,基督教要求认同以上所有命题,因此需要一个精准的神义论。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基督教的上帝被认为是有位格的、全能的和全爱的[8],才会出现问题。
另外,区分道德恶与自然恶也很重要。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道德恶直接归因于理性的自由意志, 是指那些自愿的错误行为,例如撒谎、偷窃、谋杀、虐待、强奸等。就此而言,任何自然恶都假定有一个绝对的元伦理学标准,据以判断善恶。而自然恶却不是由人为的原因带来的,可以称之为非道德的。自然恶包括气象灾害、多数的躯体病患或者动物的袭击,导致众生受苦、受损或死亡。以前的共识是,道德恶和自然恶都是对上帝完美创造的入侵。但是,现代地质学理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概念,比如深度时间、人类出现之前的痛苦、死亡和物种灭绝等。若是如此,我们将如何捍卫上帝及其所造之物的良善?
在上一章中,詹姆斯·斯坦博(James Stambaugh)对神义论作了概述。本章我们来探讨路德、加尔文和卫斯理的观点,看他们如何影响19世纪初期有关创世年代的争议。霍尔(Hall)在第二章中表明,从宗教改革到莱尔(Lyell),教会基本上将创世记第1到11章的内容视为真实的历史,认为创世周是近期发生的,由六个正常的日组成,而且洪水是全球性的灾难。路德、加尔文和卫斯理也完全认可这种观点,认为创世记1:31不允许堕落之前就存在[9]自然恶。已故的E. L.马斯(E. L. Mascall)断言,直到最近,
“几乎所有人都普遍认为,道德和物质上的所有邪恶……从某种角度说,都是从第一个过犯衍生出来的,即一个被赋予理性的受造物故意与他明知的上帝旨意背道而驰。”[10]
换句话说,在现代地质学和圣经研究中的“高等批评”理论出现之前,大多数人认为自然恶是源于罪。潘柏滔(Pattle Pun)将这种自然解读创世记的共识描述为“对创世记记载的最直接的理解,不顾及科学(例如地质和天文学)所带来的所有的解经学考量。” 潘补充说这个共识就是:“上帝在六个太阳日之内创造了天地……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死亡和混乱进入了世界,所有化石都是灾难性的全球性洪水的结果。”[11]
但是,均变论则从化石层的地质记录中读出血腥的历史;[12] 他们宣称这些石头在哭诉自然历史状况似乎并不“甚好”。新出现的理论框架认为:在深度时间的残酷现实中,早在人类堕落之前,非人类领域中就曾存在痛苦、竞争、捕食、疾病、死亡和灾难性的大规模灭绝。这种理论被当作有据可依的历史真相来宣讲,为从未面对过古自然恶思想的教会带来了新的神义论上的压力。[13] 如果自然恶先于亚当而存在(脱离了与原罪的刑罚关系),那么信徒们就需要论证为什么上帝及其创造仍然是美好的。在教会对上帝良善的认识上,地质学会引发一个重大转折吗?
对于这个问题,19世纪初期的英国有两派思想。传统主义者坚持长期以来的观点,认为人类堕落影响了整个创造,自然恶是对原始创造的入侵。而包容主义者则试图把深度时间嵌入创世记,自然恶就只能被视作非侵入性的。创世记和地质学在神的创造活动上各有说法,针对这个问题的严重分歧表明了自宗教改革时代以来教会在观念上的重大转变。
原始受造的秩序和伊甸园诅咒的影响——早期新教徒的观点
为了比较这些始于19世纪初期的对立观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路德、加尔文和卫斯理这三位主要的新教神学家对自然恶起源的理解,以作参照。他们的思想将提供一个历史观察点,用以与后来的神义论做比较。
马丁·路德(1483-1546)
路德用了十年时间为创世记写评注,可见他是多么重视这卷书,并将之视作理解圣经其余部分的基础。他专注于创世记的字面意思,并对俄利根(Origen)、耶柔米(Jerome)和奥古斯丁(Augustine)的寓意解经倾向有顾虑。路德认为,这些作家“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寓意上”,诱使一些人
“偏离了历史事实和信仰,而寓意本应该以唤起、增强、启发和坚固信仰为目的,因为每一件历史事实都指向信仰。至于那些不注重历史记载的人,难怪他们会寻求寓意解经这条捷径并沉浸其中夸夸而谈。”[14]
关于创造日,路德认为,摩西所说的“白天和黑夜”显然就是通常我们所认为的白天和黑夜,没有寓意。
“我们确信摩西是指字面意义上的、而不是寓言或比喻的意思。也就是说,如经文所记载的,这个世界及其所有的生物都是在六天内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解其因,那我们就要甘做小学生,让圣灵教导。”[15]
路德是如何看待罪对自然的影响的呢?他就许多推测性的异议向我们发出警告,因为创世记记录了“犯罪和大洪水之前的历史”,而“我们只能谈论犯罪之后和大洪水之后的情况。”[16] 荆棘和蒺藜不是“未受破坏的创造物”[17]的一部分,而是因罪而来的。[18] 对于路德来说,若非因为堕落,“地球可以生长一切,不需播种和耕种;”地球“会乐于生产最好的物产,但被诅咒阻止了”;地球也不会有寸土荒芜,而是所有的土地都会保持“惊人的肥沃和生产力”。但事实是,种植业被杂草困扰,更别提“来自天空的搅扰、有害的动物及类似的无尽的麻烦,所有这些都在增加……悲伤和苦楚。”[19]
路德说,即便是有害的昆虫也源于罪。[20] 在回答关于“害虫和有害动物”的提问时,他说,这些在人类堕落之前是不存在的,而是作为对罪的一种惩罚才来到世上。”[21] 请注意以下重要宣称:
“狼、狮子和熊不会获得众所周知的野蛮性格。在所有创造中,绝对没有任何东西会给人类带来麻烦或害处。因为经文清楚地指出:‘神造的一切都甚好。’但是看现在有多少麻烦!有多少疾病困扰着我们的身体!……其它凶猛有毒的动物带来的危险有多大!”[22]
路德认为,在人类没有犯罪的时候,受造界完美地和平共处。如果人类保持顺服,“就不会惧怕洪水泛滥。”[23] 他认为,如果说亚当可能会“杀死一只小鸟当饭吃”,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24] 在“因罪而堕落”之前,受造界是“完全不同的”,而是处于一种纯真无邪的完美状态;[25] 一个黄金时代,“既无荆棘,也无蛇或蟾蜍,即便有,也无害无毒。”[26] 类似地,“水、火、毛毛虫、苍蝇、跳蚤和臭虫”等也“向我们讲述着罪恶和神的愤怒,因为它们在人犯罪之前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无害且不会带来麻烦的。”[27] 因此,受造界的纯洁无瑕取决于亚当和夏娃是否维持纯洁无瑕。
“如果亚当没有吃禁果,他将永远不死。但是由于他不顺服而犯了罪,就屈服于死亡,像动物屈服于他一样。[28] 最初,死亡并不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他之所以死是因为他激怒了上帝。就他而言,死亡是他犯罪和不顺服的必然和应得的后果。”[29]
路德继续写道,亚当在纯朴的状态下本是“无罪、不死、[30] 免于咒诅的。”[31] 罪不仅影响了亚当,而且“由于罪恶,世界也开始变得不同;也就是说,受造界的堕落和被咒诅是随着人类的堕落而来的。”[32] “无穷无尽的邪恶”进入了世界,皆因“原罪的严重”。[33] 所有“有害的植物……诸如毒麦、野燕麦、杂草、荨麻、荆棘,以及毒药、害虫和其他任何此类东西……都是因为罪而被带入受造界的”。[34]
在评论有关罪恶的见证时,路德感到“几乎整个受造界都充满了这样的见证,”[35] 因为大洪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造山运动,因此山脉也在提醒人上帝的愤怒。令路德感到震惊的是,尽管上帝的愤怒在大地和每个生物体中都显而易见,但我们却有着一种“自鸣得意,漠不关心的态度”。[36] 有趣的是,对于路德来说,大洪水是“更严重的诅咒”,彻底摧毁了“天堂般的世界和整个人类”。[37] 这场大灾难使得我们丝毫看不见世界最初的模样,[38] 以致于路德设问:“如果现在的河流泛滥都会对人类、牲畜和田野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一场世界范围的大洪水又将如何呢?”[39]
约翰·加尔文(1509–1564)
加尔文也认为,创世记讲述的是近期发生的、字面意义上的六日创造和全球性的大洪水。加尔文在反驳“世界是在一瞬间被造”的谬论[40]时,他写道:
“如果说摩西仅仅为了教导(周期性作息)的目的,就把上帝一瞬间完成的工作分成了六天,这也实在太牵强。我们宁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花了六天的时间,是为了使他的工作与人类的能力相匹配。”[41]
谈到地球年龄,加尔文明确地表示,地球的年龄不超过6000年。加尔文写道:“一开始就标记了时间,这样,根据岁月的延续,信徒就可以找到人类和万物的最初源头。”[42] 这听起来很像是在为乌雪(Ussher)做铺垫。加尔文认为这一认知是:
特别有用的,不仅有助于抵制从前在埃及和其他地区盛行的荒谬神话,而且一旦知道了宇宙的开端,上帝的永恒性就可以更加清晰地显明出来,我们也许会更倾向于思考这一点。以下这个不敬虔的讥笑实在不应该打动我们:很好奇‘创造天地’这个主意为什么没有早点进入神的脑海?神让大量的时间白白流逝,因为他原本可以早几千年创造出天地来,尽管世界的年龄还不到6000年,而且如今已趋终结。”[43]
他警告说,当这些“不敬虔的讥笑者”妄下论断,“因为神没有按照他们的判断在很久以前创造宇宙,就指责上帝碌碌无为。好像这六千年来,上帝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让我们用心认真地思考。这种情况[六天的创造]让我们脱离虚幻,转向唯一的上帝。他将创造的工作分配到六天之内,这样我们用一生去思考也不会觉得厌烦。”[44]
加尔文坚信光是先于太阳被造的,亚当是用尘土造成的,而夏娃则是用他身上的一根肋骨造成的,[45]人的堕落使咒诅临到了所有的受造物,所有不在方舟上的有气息的陆栖动物都死了。[46] “(挪亚时代)遍地充满了混乱与无序”,加尔文认为上帝“有必要进行一些翻新。”[47]
谈到自然恶,加尔文认为“极端的天气、霜冻、雷电、不合时宜的雨水、干旱、冰雹以及任何无序的事物”[48]都归因于人类的罪。简而言之,
“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所有事物都处于混乱状态。我们因自己的罪而使天地都陷入混乱。如果我们按正确的秩序顺服上帝的话,毫无疑问,所有的其它受造物都将依从我们,因此我们应该能达成……天使般的和谐。”[49]
关于弱肉强食,加尔文问道:“凶残者的凶残是从哪里来的?强者以可怕的暴力将弱小的动物抓住、撕裂并吞吃,这种残酷的本能从何而来?”[50] 他认为,如果“罪没有污染世界,那么按照上帝所命定的方式,没有任何一种动物会沉迷于猎杀取食,相反,地上的果实将满足所有生物的需要。”[51]
对加尔文来说,堕落使“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败坏,并带来“最污秽的瘟疫、盲目、软弱、不洁、虚浮和不公。”[52] 亚当“败坏了天上和地下的整个自然秩序,因此他的叛逆把人类引向毁灭……无疑(这些生物)承担了人类应得的部分刑罚,而这些生物原本是为人类而造的。”[53] 由于罪,“土地的生产力减弱,出现刺、荆棘和害虫”,[54] 原本驯良的动物变得野蛮并具威胁性,并且“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愿如此,而是由于我们的过失。”[55] 因此,加尔文断言,目前观察到的自然恶是扭曲畸变的结果,而非原始世界的一部分。随着亚当从其最初的状态中堕落,
“世界也必然逐渐从其本性中退化。关于现存的跳蚤、毛毛虫等其它有害的昆虫,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们不是源于上帝的手,而是出自人的罪。的确,这些生物也是神创造出来的,但也是神惩罚我们的一种方式。”[56]
加尔文进一步确认,“如果不是因为人类犯罪而受咒诅,整个地球会如起初所造时那样硕果累累、喜气洋洋,倍受神的祝福。简言之,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畸形状态相比,那样的景象和乐园没有什么差别。”[57]
谈及荆棘和蒺藜的来源,加尔文写道,世界“将和以前不一样,不再出产完美的果实。因他宣称地球的肥沃程度将退化,并长出刺和有害的植物。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无论长出什么样的不良事物,那都不是地球的自然成果,而是源于罪恶的败坏。[58]
因此,加尔文神义论的关键点在于,所有的自然恶都源自罪。这与路德的观点一致。
约翰·卫斯理 (1703-1791)
卫斯理并未在创造日的长短上详细论证,很可能是由于这个问题看起来太明显,无需辩护。但他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我们不要去想上帝本可以在瞬间就创造出世界,却用了六天。我们要想他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显示他的自由,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里,做自己的工作;也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他的智慧、能力和良善,让我们可以思想这些;他更为我们树立了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的榜样。”[59]
卫斯理肯定地说,大洪水是在“挪亚600岁”和“创世1656年”[60]的时候发生的。从他对创世记7到9章所做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与路德和加尔文持有相同的观点,把大洪水的细节当作真实的历史。
卫斯理认为,罪败坏了一切受造之物。他写道:根据上帝“自己的宣告,我们有十成把握,世界上本没有自然恶,直到作为对罪的刑罚,恶才来到世界上。”[61]他注意到上帝称刚刚造出的一切是“甚好”,[62] 而对于目前事物的状态,卫斯理写道:“整个物质世界处于何种状态!且不说无生命的自然界中的每个成分都处于失控状态,轮流与人类作对;自从人类悖逆他的创造主,整个动物界处于什么样的状态?”[63] 卫斯理认为,在人类犯罪以先并不存在自然恶。[64] 堕落使所有生物“屈服于虚空、悲哀、各种痛苦、各样邪恶”。[65] 关于“事物在目前的状态”[66]以及上帝怜悯所有活物的预设,卫斯理问道:
“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邪恶压迫着它们、让它们难以忍受呢?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在地球上蔓延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各个时代最聪明的哲学家。如果不诉诸上帝的圣言,就无法解答这个问题。”[67]
在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上会有痛苦时,卫斯理写道:“因为有罪:如果没有罪,就不会有痛苦。”[68] 在人类堕落以先,亚当被免于痛苦、死亡[69]、疲乏[70]以及皱纹。[71] 并且,“没有猛烈的气流,没有狂风,没有恶劣的冰雹,没有暴雨,没有霹雷或叉状闪电。”[72] 在植物界,“没有杂草,没有无用的植物,没有破坏地面的植物,更没有有毒的和伤害性的植物。万物都令人心怡。”[73] 卫斯理又认为,潮汐“对任何活物都没有伤害或不健康的影响。”[74]虽然有“别出心裁的人想象”星星是“被毁灭的世界”,但卫斯理反驳道:“星星既不带来邪恶,也不预示邪恶。”[75] 卫斯理清楚地认定,我们现在的自然秩序是咒诅的结果,和原本的完美状态截然不同。[76]
卫斯理认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整个动物界都因亚当的罪而受到了惩罚。”[77] 现在,动物本性的“根基” 被完全颠倒了。[78] 原本的善良所剩无几,罪使得“成千上万的动物”变得“野蛮凶猛”和“残酷无情”,[79] 如今这些动物撕裂肉体,吸食鲜血并嚼碎骨头。[80] 现如今“绝大多数生物——也许有百万分之一的例外”[81]的秉性是
“互相吞食,征服所有能征服的其他生物。的确,这就是目前世界上悲惨混乱的状态。无数的生物若不残杀其它生物就无法保存自己的生命。但是起初并非如此。天堂般的大地为所有栖息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因而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有需要或被诱惑去捕食其它生物。那时的蜘蛛如苍蝇一样无害,无需伏击杀戮。即使最弱小的生物也可以安全地爬行……[没有什么]让他们感到害怕。同时,所有爬行动物都同样无害。没有猎食的猛禽野兽:没有彼此的摧残和骚扰,所有生物都呼吸着……伟大创造主的恩福。”[82]
对卫斯理来说,“甚好”的受造物是无需猎食也无需惊惧的,更没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血浸爪牙”的兽性。
卫斯理说,人的罪不仅将死亡带进了人类以下的世界,“而且还带进了一大串通向死亡的邪恶:疼痛及数不清的苦难。”[83] 他料到有一些人会用自然恶来攻击上帝的良善,认为这些“吹毛求疵的哲学家”和“无聊之人”[84]都是立足于一个巨大的谬误:
“认为目前世界的状态和起初一样,他们在此假设之上可以建造众多的反对意见。但当我们发现这种假设并不成立时,这些反对意见便落了空。世界起初的状态和现在所见的完全不同。因此,你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反对目前的状态,无论是对有生命的还是对无生命的受造物,不论是对普遍状态还是对任何具体事例,答案都是现成的:即它们不同于起初的状态。[85]
在卫斯理看来,上帝初造之物“比现在好得无以言表。……没有瑕疵……或缺陷。他所造的无生界里没有腐朽和损害,动物界没有死亡,也没有兆示死亡的罪恶和痛苦。”[86] 在回应索姆·詹尼斯(Soame Jenyns)关于自然恶“必然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中”的观点时,卫斯理认为,为创造者制造可悲的借口是可耻的,因为创造主“不需要我们为他自己或者他的创造物辩护。”[87] 卫斯理主张“堕落神义论”,将所有的自然恶追溯到遍及寰宇的大堕落。在回应其它诸如“如何从如此残缺的所造之物中明明地晓得上帝眼不能见的属性”之类的问题时,卫斯理声称“圣经中关于自然恶源于道德恶的阐述会轻而易举地提供完美的答案。”[88]
上文勾画出新教中三位主要领袖的思想轨迹,着重于他们解释自然恶的神义论。有了这一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考虑后人对自然恶起源的看法了。[89]
简介19世纪早期两个对立的学派
在19世纪初期,深度时间的概念被引入了对地球历史的探讨之中,这意味着关于自然恶的神义论必须面对古自然恶的问题。两个英国团体对此表达了意见,尽管他们有些一致的看法,但在三个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分歧。首先,科学和自然界是否具有与圣经同等的权威?换句话说,当科学与圣经发生冲突时,哪一方具有最终的否决权?是特殊的启示还是自然的启示? 如果两者不同等或不能兼容,是否都要屈从于第三标准,比如传统? 其次,对于有关创造和洪水的记载我们应该使用怎样的释经法?第三,自然恶的起源是什么? 倾听他们对此类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勾勒出每个派别的神义论轮廓。如果这些神义论差异很大,福音派人士应该知道哪种神义论最忠实于圣经,并且与教会历来的教导一致。
19世纪初期,最配贴上“传统主义者”这一标签的莫过于那些“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简称“圣经地质学家”。[90] 实际上,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教会内部关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兼容性的大多数争论可能源于“忠于圣经”(scriptural)这个词语。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圣经地质学家,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由于他们顽固地坚持对创世记的自然解读。看到包容主义的精神已经酝酿了半个多世纪,他们认为,如果让创世记屈从于地质学的推测,宗教改革辛苦得来的成效将被抵消。但是,包容主义者以“地质科学的可靠结果”为武器,并高举“我们从伽利略事件中学到了什么?”的旗帜,放弃了当初的改教家们赋予创世记第1-11章的历史性。
英国的主要圣经地质学家包括乔治·布格(George Bugg)、威廉·科克本(William Cockburn)、亨利·科尔(Henry Cole)、乔治·费尔霍姆(George Fairholme)、托马斯·吉斯伯恩(Thomas Gisborne)、约翰·默里(John Murray)、格兰维尔·潘(Granville Penn)、威廉·莱茵德(William Rhind)、约瑟夫·萨特克利夫(Joseph Sutcliffe)、莎朗·特纳(Sharon Turner)、安德鲁·乌雷(Andrew Ure)和乔治·杨(George Young)。[91] 他们都坚持创造日为24小时,洪水是全球性的,并就此撰写了大量著作,流传甚广;他们也否认自然恶是上帝“甚好”的创造的一部分,而认为邪恶是对完美创造的入侵。下面我们将以布格、乌雷和杨在古自然恶问题上观点为代表,略加阐述。
另一方面,我们将威廉·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约翰·派伊·史密斯(John Pye Smith)和休·米勒(Hugh Miller)列为基督教包容主义者的主要代表,因为他们巧妙地解答了自然恶的问题并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他们不认为创世记的日是字面上的,也不认为洪水是全球性的、有地质意义的,而是把自然恶看作是神的本意。
我们的讨论将着重于各派如何认识初造的“甚好”世界、自然恶的起源以及堕落和洪水的范围。[92] 地质学和释经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上帝品格的看法?通过分析他们对古自然恶问题的回应,我们希望可以追溯教会理解神的良善的微妙演变。尽管包容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确实有一些共同立场,但他们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分歧。莫腾森在第三章已经指出了他们在创造日的长短、创造的时间以及洪水的范围和破坏性方面的差异。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他们在神义论上的七大对比。
对比一:初造的世界好在哪里?
第一个不同点在于自然界在堕落前的生态和造物主“甚好”的认可。传统主义者认为,在人犯罪之前,一切都是绝对完美的,不需要任何改善,并且也没有“之前”对上帝的作品的“革命和破坏”。[93] 而包容主义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堕落之前,受造界的完美和良善是相对的。这意味着自然恶是被造的,完美地执行着其预期的目的。自然恶不仅是设计的证据,而且是善意设计的证据。
前文提及的三位神学家(路德、加尔文、卫斯理)虽然在救赎论上相差甚远,但在上帝对受造界的认可上步调一致。路德认为上帝给了人类一个居所,人在这里可以一无所缺地“过着最舒适的生活”,但可悲的是,“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因为犯罪而丧失了。”[94] 加尔文认为,如果不是因为罪的败坏,那么这个“甚好”的黄金时代将会持续下去。[95] 卫斯理认为它“比现在好得多,无言以表”,[96] 他认为堕落前世上不存在瑕疵、毁灭或自然恶。
对19世纪早期观点的论述在这里只好从略。我们的概述旨在辨别哪一派在创世记1:31上与改教家们更紧密地吻合。[97]
对比二:堕落后的世界承载了刑罚的疤痕吗?
由于两派对起初受造界“甚好”的含义各执一词,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区别:即自然界是否带着刑罚的疤痕。对于传统主义者而言,罪的后果比比皆是:从荆棘到火山、从害虫到猎食、从疾病到死亡。在堕落之前,气象学、地质学或生物学各领域里都看不出动荡。因此,在犯罪之前,既没有地质物理灾难,也没有动物的痛苦和死亡。
包容主义者认为,罪并没有或者鲜有带来自然界的败坏。火灾、冰雹和雪灾等都是出于创造世界的“同一位造物主的意志”。[98] 此外,招致痛苦、死亡和灭绝的系列灾难也都是有意的、必要的和预备性的,从起初就被编织在受造界的原始蓝图中。随之而来的附带损失是为了实现更好目标的不可避免的代价。任何关于“黄金时代”的想法都是包裹在字义主义的天真面纱里的纯粹的怀古情结。
但卫斯理认为,受造界本来是“处于与我们现在所见的世界完全不同的状态。”[99] 加尔文也认为自然恶代表着原始受造界的腐朽和堕落,以致于“现在所看到的世界上的许多东西,与其说是其原本所有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是败坏。”[100] 这类神义论理念并未为后来的包容主义者所采纳。
对比三:深度时间系列灾难的起因
另一个明显的对比是地球物理大变革的起源。传统主义者认为次生地层中没有灾难性的动荡。[101] 只发生过一次灾难性的大洪水,大洪水造成了大部分的地质柱及其中含有化石的地层。
但包容主义者认为大洪水只是许多灾变中的最后一个,每场灾变都可能导致大规模灭绝,但没有一次是全球性的。亚当之前的那些灾变共同构成了地质柱及富含化石的岩层。这些人还认为,人类犯罪后自然界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地球物理学改变。万物都象起初一样在延续。
路德认为,在犯罪之前没有“地面沉降”或“地震”。[102] 卫斯理推测将来会复原到堕落前的状态,届时再也不会有“震荡或破坏性定律,例如地震、恐怖的乱石或险峻的悬崖”。[103] 相较之下,传统主义者与改教家们的立场相吻合。但是包容主义者教导在人类犯罪前曾发生多达五十次的地球物理大变革,违反了改教家们关于初始受造界的宁静以及这个和平王国因犯罪而败坏的主张。
对比四:躯体疾患的起因
第四个对比是疾病的根源。疾病是犯罪的后果,还是从第一日就纳入了设计师的蓝图中?杨代表了传统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圣经教导说罪“将死带入了世界,并伴随着所有的痛苦。”[104] 他以为创世记教导“受造物所遭受的苦难和毁灭是人类过犯所带来的众多苦果的代表,”[105] 若有人说“痛苦”先于罪而存在或在深度时间内一直发挥作用,他会将这种想法贴上不符合圣经的标签。
包容主义者(如巴克兰)认为自然界“充斥着死亡的证据”和物种的灭绝,[106] 这与人类的错误行为“没有丝毫关系”。[107] 他认为,上帝诅咒中的刑罚“严格地且仅仅”限于人类,[108] 这在逻辑上把上帝当成了人类以外的领域中所有疾病、痛苦和死亡的始作俑者。
卫斯理坚信,由于罪,生物“屈服于虚空、悲哀、各种痛苦、各样邪恶”,[109] 而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邪恶”。[110] 路德经常提及疾病的原始成因在于原罪。加尔文也认为“疾病的基本原因”是罪。[111] 伊甸园里的堕落扭曲了受造界的每个部分,使受造界到处充斥着“最污秽的瘟疫、盲目、软弱、不洁、虚浮和不公……痛苦”。[112] 是传统主义者还是包容主义者在神义论上与宗教改革的先贤一致,还请读者自己判断。但是包容主义者们似乎已经开拓出与路德、加尔文和卫斯理的主张大不相同的神学上危险的疆土。
对比五:捕食的起源
另一个对比与捕食有关。传统主义者认为伊甸园里是没有掠食的,所有动物都是草食动物。[113] 鲍格认为,上帝原本“给所有动物只提供了菜蔬作为食物”,[114] 但是后来退化成食肉状态,其余的提法都是“对上帝智慧和良善最大的侮辱”。[115] 这与路德等人的观点一致,即食肉是大堕落的直接结果。[116]
包容主义者抹去了肉食与堕落的联系;他们认为捕食远早于人类。巴克兰认为肉食成全了“生命的毁灭”;[117] “普遍死亡定律是一种既定的状态,是造物主欣然赋予……地球上每个生物的”。[118] 米勒以为,用来切割、穿刺、折磨和杀害的掠食性肢体结构从起初就一直为这些目的而存在并发挥着作用。[119] 史密斯认为亚当之前没有食肉动物的想法是难以置信的。他声称“在千万种情形下,[食肉]直接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利益。”[120] 在捕食的问题上,传统主义者再次与先贤保持一致,而包容主义者则更受地质哲学而非释经学的驱动,采纳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对比六:人类和动物死亡的原因
与上一个对比类似的第六个对比是:人类和动物的死亡是预设的还是侵入性的。传统主义者的学说认为死亡是由于刑罚。鲍格认为所有的死亡都是原本完美的受造物全面堕落的一个方面。人类从被造时的完美状态中堕落,其他生物也随之一起堕落,人类的天性趋于恶化。”[121]
然而,包容主义者认为死亡是“生命必经之路”,他们认为“石头呼喊”的就是这个合理的解释,而非其它。死亡从一开始就被放置在受造界的各个层面。关于人类死亡的起源,包容主义者暗示,如果人类从未犯罪,就不会品尝到肉体死亡的滋味。但是他们并不像传统主义者那么明确,也不排除在神的设计中所有生物都要死亡。
卫斯理、加尔文和路德在食肉的起源上看法一致。加尔文提到罪的“可怕的诅咒”时说:“天地间所有无害的生物都因我们的罪遭受了惩罚。”[122] 卫斯理甚至说,即使在昆虫界,堕落前也不会有死亡(至少不是被捕食)!
伊甸园的国度里为“所有栖息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有需要或被诱惑去捕食其它生物。那时的蜘蛛就如苍蝇一样无害,无需伏击杀戮。即使最弱小的生物也可以安全地爬行……[没有什么]让他们感到害怕。同时,所有爬行动物都同样无害。没有猎食的猛禽野兽:没有彼此的摧残或骚扰:所有生物都呼吸着……伟大创造主的恩福。”[123]
传统主义者、包容主义者和改教家们在人类死亡的起源上有一些统一的认识,但是在古自然恶和动物惨死的问题上的观点却大相径庭。传统主义者认为捕食现象与创世记相违背,但是包容主义者允许堕落前的世界里“血浸爪牙”,[124] 他们甚至不反对人类的死亡也是上帝设计的说法。
对比七:透过古自然恶看上帝的品格
所有上述的对比都是为这一对比作铺垫:古自然恶对我们所谓“上帝的面孔”的影响。大多数基督徒同意史丹利·赖斯(Stanley Rice)的设想,即“造物主想通过受造界呈现他的部分品格,以便我们可以了解他。”[125] 我们探讨过的19世纪的六个人物都同意:最初的受造界彰显了上帝的能力、智慧和仁慈。但是,其中一部分人说目前的受造界因为人类的罪而处于堕落状态(传统主义观点),而另一派则说现存的受造界正是全爱、全能的上帝从一开始就有的本意(包容主义观点)。这两种观点为良善的上帝描绘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形象。
对于鲍格、杨和乌雷来说,将血雨腥风的自然界中的苦难解释为最优设计,而且说这是仔细研读圣经的结论,说我们只能指望上帝如此设计,这在神义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这当然不是路德、加尔文和卫斯理所拥戴的上帝。一个全善的、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拥有所有可能的选择来创造万物,为何竟然喜悦这样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如果不是邪恶地)设计出深度时间、系列灾难、痛苦、疾病和死亡,来创造并维持着有意识的受造物呢?对于这样一个手如刀锯的设计师,你能说他什么呢?
包容主义一类的神义论指向一个无情的造物主,现代怀疑论者对此表示惊讶。鉴于某些有神论者拥戴“自然选择之神”,20世纪著名的无神论者贝特朗·罗素有如下思考:
“宗教……已经迁就了进化论的教导……有人告诉我们……进化是一种想法的施展,这种想法一直存在于上帝的头脑里。看来在那些年代……当动物用凶猛的角和惨痛的刺互相折磨时,全能者在静静地等待着。为什么造物主宁愿通过一个过程来达到他的目标,而不是直接去实现它呢?这些现代神学家并没有给出解答。”[126]
哲学家戴维·赫尔(David Hull)也同样疑惑,他指出自然选择的过程“充满随机性、偶然性、不可思议的浪费、死亡、痛苦和恐怖……自然历史资料所提示的上帝不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粗心、冷漠、几乎是恶魔般的。”[127]
诺贝尔奖获得者、无神论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认为自然选择是“一个可怕的过程”,他惊讶于“基督徒会捍卫这样的想法,说这或多或少是上帝设立的过程”。[128] 知名生物学家狄奥多西·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自称既是创造论者也是进化论者,他也表示:
“宇宙在受造时本可以处于完美状态。为什么有这么多错误的分化、灭绝、灾难、痛苦,而且最后都要面对最大的恶——死亡?这一切不可能都是慈爱怜悯的神所计划的。任何将进化视为上帝预定或引导的教义都会与邪恶存在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产生正面冲突。”[129]
之后他补充说:“从上帝的角度来说,从无到有地制造大量物种,然后让大多数物种灭绝,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造物主在闹着玩儿吗?”[130] 我们同意,这样的作为与慈爱的创造主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不一致。
考虑到罗素、赫尔、莫诺和杜布赞斯基主张背后的含义,读者也许会同意以下理念:传统主义者捍卫六日创造、字面上的堕落和全球性洪灾可能主要是出于捍卫上帝品格的需要,而不是像人常常论断的前科学的、傀儡般的对愚蠢的文字主义的坚持。圣经地质学家们肯定是这种情况。鲍格很明白这一点:
“因此,我们与印度教放肆邪恶的观念达成了一致,那就是上帝‘一次又一次地,好像闹着玩一样,创造和摧毁了世界’!一个智慧、公义和仁慈的神‘无数’次地创造了奇迹,然后仅仅为了消灭整代动物而摆脱了他通常的方式,以便他可能创造出与祖先类似但略有不同的生物!任何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和相信全能的上帝从不创造‘多余的奇迹’和白白做功的哲学家们,会倡导这样的荒谬论调吗? ”[131]
格兰维尔·潘在这个论点上讲得极为深刻,深入思考以下这段语录将使您受益匪浅:
“先验地、武断地假设上帝将地球上的物质创造成最不完美的状态,而且这状态是人类粗浅的想象力就可以杜撰出来的。如此,人们把神发出的创造命令降级为仅仅造出某种无定型的初级物质,进而假想神的才能和智慧表现在某些假设的神秘法则中,通过这些法则,历经无数岁月后,无定型的物质自我改进以至于形体和组织上的完美。如果这样的假设不招致巨大的反作用力,弹击在臆测者自己身上,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粗陋无理,其后果必将削弱我们对于神的智慧和能力的认识。这种假设完全是随意的,不仅是随意的,而且是恶意的,因为这完全没有必要,而是流露着恶意的选择。因为,物质界的法则不可能在造物主所造的(据称)不完美的物质中发挥作用而使之完美,除非通过制定法则的造物主亲自赋予的权能。再者,如果他能通过法则的运作而间接地实现完美,那他就可以不通过法则的作用而直接地实现完美。那么,为什么要在没有援引任何权威的情况下放肆地、恶意地选择需要中介法则的假设呢?这个决定完全是选择和偏好,是个人意愿,因为这与理性无关,理性既不会敦促、建议、鼓励,也不会以任何形式助长或诱发这种决定,相反,理性会积极地否认和谴责之。要捍卫这种险恶的选择就必须引入漫长的时间,而对于造物主来说,只有在克服某些阻碍完善过程的困难时才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这些人假定他在物质中制造了障碍,来抵制和延缓他所设计的作品的完善;而同时他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行为而毫无阻拦地完善他的作品。这些人没有丝毫出于理性的动机,先验地假定智慧的上帝一方面定意造就完美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又设置一系列障碍来拦阻和延迟该完美作品的完成,这分明显示哪个地方有严重的智力缺陷,至于该缺陷是在造物主身上还是在臆设者身上,还请学界诸君定夺。”[132]
虽然包容主义者试图将上帝从古自然恶所隐含的恶味中开脱出来,但他们似乎不为古自然界死亡的惊人数量所动,可以在造物主认可的“甚好”世界中包容任何程度的(非人类的)痛苦、死亡和大灭绝。这样的信徒似乎准备给上帝一个免责通行证,“即使他让世上的痛苦增加十亿倍。”[133]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潘葛洛斯式的[134]神义论,让创世记1:31包容任何程度的自然恶,会让怀疑论者佩服吗?
本研究的七项发现
1. 古自然恶是19世纪初公认的难题
随着深度时间的地质学解释逐渐扎根,解释古自然恶的神义论成为必要:基督教的上帝会故意设计这样一个充满“随机性、偶然性、不可思议的浪费、死亡、痛苦和恐怖”的过程吗?
2. 对古自然恶问题的回应分为两个基本派别
19世纪初的神义论有两个主要学派:传统主义者和包容主义者。两派的主张对比鲜明,基本上反映了当今的争议:命定创造论(年轻地球倡导者)还是渐进创造论或神导进化论(深度时间支持者)。
3. 有些人认为古自然恶与创世记的直白解读相冲突
传统主义者认为古自然恶让神的形象大打折扣,并敦促教会忠实于圣经的字面意义。这群人的明显动机是拥抱原初的圣经读者最可能认定的历史事实。当圣经和地质学之间发生所谓的冲突时,传统主义者提出了对地质证据的合理解释,而不是牺牲对创造、堕落和大洪水记录的自然解读。将创世记与一个年轻的科学分支的不断演变的理论捆绑在一起,这样的释经学对于传统主义者来说简直是无法接受的。
4.有些人认为古自然恶与创世记相一致
相反,包容主义者在释经学上采取了更灵活的做法,把古老地球的理论与圣经结合起来。他们不仅认为古自然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且认为古自然恶没有损及造物主良善的属性。在打造与古自然恶相适应的神义论、神学和释经学架构时,他们的神义论表现出强烈的潘葛洛斯色彩。
5.传统主义者的神义论与早期新教的神义论相吻合
19世纪初的传统主义者的神义论观点与早期对神的仁慈的经典理解是一致的,因为神的仁慈通过创世的方法揭示出来。像路德、加尔文和卫斯理一样,圣经地质学家认为剧烈的痛苦、死亡或自然恶在“甚好”的受造界里没有一席之地,而是堕落后侵入的。毫无疑问,改革者和传统主义者拥戴相同的神义论纲领。
6.包容主义者与早期的新教神学几乎没有连贯性
包容主义者认为自然恶被故意设置于“甚好”的受造界中,而非外来的入侵。既然割裂了罪与死的关系,他们就不得不采用与改革者的观点大相径庭的潘葛洛斯式的神义论。
7、针锋相对的神义论描绘出截然不同的上帝形象
最后,这些关于神创造的方法的截然不同的哲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理念上和历史上的多重视角,帮助我们追溯上帝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的演化,或说,帮助我们看出从改革时代到19世纪初,人们对他的仁慈的理解的转变。[135] 本章显示,传统主义者认识到古自然恶所带来的严重的神义论难题。尽管上述两派九位主要思想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上帝的良善可以从对自然的研究中推演出来,但他们在如何构筑这种良善方面各执一词。“上帝的面孔”的比喻将传统主义者的上帝与包容主义者的上帝区分开来。传统主义者所描绘的神的“面孔”令人向往,反映出温柔的同情心和呵护的恩典。但 “深度时间”的上帝面容虽然可以经过潘葛洛斯式的整容,但其自然流露出的一大堆表情并不给人以慈父般的安适、智慧和道德正义感。
随着新地质学的发展,包容主义者“在处理创造过程中的痛苦、疾病、灾难和死亡这一棘手的问题时”显得过分乐观了。“一般地说,他们要么忽略问题,要么敷衍了事,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将邪恶归因于神的仁慈。”[136] 他们只能将古自然恶看作神创世的方法所带来的蒙福状态,而不是罪的结果。这样他们就步入了一条私意解经的道路,把深度时间的系列灾难、痛苦、死亡和灭绝套在了摩西的记载中。
相反,路德、加尔文、卫斯理和传统主义者捍卫了一位充满爱心的造物主,他创造了一个反映出他自己的善与爱的本性的作品,因此必然没有疾病、死亡和自然恶。传统主义者反映了改教家们用来捍卫一个“甚好”的受造界的神义论。他们虽然与包容主义者共享同样的硬数据,却欣然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岩石。他们提出异议,认为均变主义所暗示的古自然恶与创世记的清晰解读相冲突,认为对自然恶起源的这种扭曲的看法可能会诱使信徒去接受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关于地球历史和上帝本性的想法。
总结
总而言之,我们在上文中的评估和简要的历史分析支持如下结论:19世纪初期对化石地层的解释引发了对邪恶起源的重新评估。起初的重新校准可能非常细微,但是却树立了坏榜样,因为到19世纪中叶为止,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骨骼化石被发掘。然而,尽管高度集中的骨床尚未发掘(如南非的卡鲁构造[137]),自然恶与上帝品格之间的不相容性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尖锐的趋势。
本章重点从几个方面对比了两群基督徒和他们对下面这一问题的回应:如果自然界在深度时间内都是血雨腥风,那么为什么上帝会称其为“甚好”呢? 如果古自然恶被认为是“甚好”的,那么可以说新地质学为上帝描绘了一张新的、远离传统上所认识的全善的面孔,而且原始受造界的美好也需要重新理解。路德、加尔文、卫斯理和19世纪的传统主义者所推崇的造物主与包容主义者的上帝大相径庭。包容主义者认为上帝会让整个物种充当进化高速公路上被碾轧的牺牲品,而且这就是它们被造的主要目的。[138]
自从莱尔时代以来,地质学所发现的自然恶的程度令人震惊,因此必须询问包容主义者在其神义论中还有多少让步的余地。他们放弃了久经考验的对创世记的自然解读法,以俯就深度时间的所谓科学事实,我们必须问:好意的福音派人士是否为进一步容让所有将来的科学共识创造了先例?当科学界说他们无法相信斧头能在水中漂浮、红海能被分开、太阳能静止不动、或者耶稣能真的在水上行走时,这些信徒将怎么办?我们一旦允许任何一门科学学科凌驾于圣经之上,有什么一致的理由拒绝它的得寸进尺呢?由于现代包容主义者在这里仍然模棱两可,“上帝的面孔”再次演变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请回顾前面关于上帝希望我们从受造界中发现他的性格的提议,[139] 将之与包容主义者关于上帝设计了系列灾难、自然恶和死亡的论证相结合,然后再为他完成的工作加上“甚好”的标记。如此一个上帝的面孔何以使他们——历史上亿万个先天性畸形者、被癌症夜以继日地折磨的活物,和最近遭受创伤的四川地震幸存者安心?
按理说,当生命经历悲剧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用相关经文或引用某些名人针对创世记1:31的语录来回应。痛苦中的人应受到更正确的善待。关怀的分寸应始终由圣灵引导、多方进行、因人而异、而且不能敷衍了事。但是,当好人遇到坏事时,福音派人士应该恢复并且接纳早期教会和改教家们认为经文中不证自明的神义论,即所有自然之恶都是罪的结果,它们在起初的受造界中并无一席之地。从牧养的角度来说,当然需要分享更多的内容。但是,确认这种肉中之刺不是造物主最初的意愿具有很大的医治作用。而现代包容主义者认为死亡及其同伙在某种程度上都“甚好”(由天上的医师设计和称谓),很难期望他们的临床关怀方式能给疼痛的心灵注入希望。当遭遇各种各样的自然恶时,秉持与卫斯理相同的观念即“起初并不是这样”,从神学和牧养的意义上讲,不是更加健康吗?
[1] 这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中国历史上还有以下地方发生过大地震:直隸1290年9月(死亡十万人);甘肃1920年12月16日(死亡二十万)和1932年12月25日(死亡七万); 西宁1927年5月22日 (死亡二十万);云南1970年1月5日(死亡一万)和唐山1976年7月28日(非官方估算,死亡六十五万五千)。
[2] 1697年, Gottfried Leibniz 在一封信中首次将希腊文的 God 和 just 放在一起组成新词 théodicée. 其想法是:鉴于种种邪恶的存在,我们如何“为上帝辩护”,维护其全能和全善的形象的完整?
[3] Stephen T. Davis, ed., Encountering Evil: Live Options in Theodicy (Atlanta, GA: J. Knox Press, 1981), p. 5.
[4] Donald Bloesch, God the Almight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5), p. 128.
[5] Robert Farrar Capon, The Third Peacock (Garden City, NY: Image Book, 1972), p. 18.
[6] Emil Brunner,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Philadelphia, PA: Westminster, 1952), p.176f.
[7] 英文 “Infallibly benevolent” ,是指完全仁慈、完全道义、完全无限的善良。神的全善性(omnibenevolence) 是指神无限的慈爱,他的内在本质将他置于一切道德罪责之外。
[8] 即,神自称是怜悯的造物主、慈爱的父亲,其关爱的范围及于麻雀和野地的百合花(马太 6:26–30, 10:29–31)。
[9] 英文”Prelapsarian”, 意思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而 “postlapsarian” 则指堕落之后。
[10] E.L. Mascall, Christian The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 (New York: Ronald Press Co, 1956), p. 32.
[11] Pattle Pun, “A Theology of Progressive Creationism,” Perspective on Science & Christian Faith 39 (Mar. 1987), p. 14.
[12] 世人的共识是地球大约有45亿年的历史,自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认定地球是均变的。传统的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声称,过去有五次大规模的灭绝,每一次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物种消失。根据公认的进化年代,灭绝发生于奥陶纪晚期(4.4亿年前)、泥盆纪晚期(3.65 亿年前)、二叠纪-三叠纪(2.45 亿年前)、三叠纪(2.10 亿年前)和白垩纪-第三纪(0.65亿年前)。进化论者声称:每一次灭绝“事件”都杀死了当时活着的生物的60%至90%。
[13] 我在2001年创造了“paleonatural evil”(古自然恶)一词,意指地质柱中所反映的古代自然恶,如大规模灭绝、进化死胡同及所谓的亚当前的掠食和死亡。古自然恶包括在深度时间内所发生的全部物理事件、事物及其状态,据信发生在亚当被造之前,造成了众生的痛苦、死亡或严重损害。
[14] J. Pelikan, ed., Luther’s Works, (St. Louis, MO: Concordia, 1960), 2: p.164.
[15] Pelikan, Luther’s Works, 1: p. 3, 6.
[16] 同上,第88页。
[17] 同上,第77页及第206页。
[18] 同上,第76页。
[19] 同上,第205-206页。
[20] 同上,第72页。
[21] 同上,第54页。
[22] 同上,第77页。
[23] 同上。
[24] 同上,第2卷第134页。
[25] 同上,第1卷第78页。
[26] 同上,第77页。
[27] 同上,第208页。路德在这里提到的水,当然是指带来灾害的水,如泛滥、溺毙和洪流。
[28] 我们必须注意,路德确实容许堕落前有动物死亡,“不是因为上帝对它们有怒气”。相反,死亡对它们来说就是……一种暂时的损害。这确实是上帝命定的,但不是……作为惩罚。动物之所以死是因为出于其它原因,上帝认为他们应该死 (同上,第13卷第94页)。
[29] Pelikan, Luther’s Works, 13: p. 94.
[30] 路德认为,虽然人类免于疾病和死亡(甚至头上不生皱纹),但他最终将“从肉体的生命转变为属灵的生命” (Pelikan, Luther’s Works, 1: p. 92)。
[31] Pelikan, Luther’s Works, 1: p. 89. 路德认为在最初的世界中没有中风、麻风、癫痫和其他恶性疾病,如“蛇腹”或“脑虫”(同上,第1卷第92页)。
[32] 同上,第1卷第77-78页。
[33] 同上,第1卷第71页。
[34] 同上,第1卷第204页。
[35] 同上,第1卷第209页。
[36] 同上,第1卷第208页。整个受造界都是对原罪的集体控告。但是有些释经者仍然能够对此事实保持“惊人的麻木”(同上,第209页)。
[37] 同上,第1卷第90页。
[38] John Nicholas Lenker, ed., Luther on the Creation (Minneapolis, MN: Lutherans in All Lands, 1904), 1: p. 164.
[39] Pelikan, Luther’s Works, 1: p. 90.
[40] 鉴于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一书中论及奥古斯丁,很可能他的心里主要是指奥古斯丁。参见 Valentine Hepp, Calvi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30), p. 203–204.
[41] John Calvin, Genesis [1554], trans. and ed. John King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84), p. 78.
[42]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J.T. McNeil, ed. (Philadelphia, PA: Westminster, 1960), 1: p. 160.
[43] 同上。
[44] 同上,第1卷第161页。
[45] 尽管这种造女人的方式对“亵渎神的人”来说似乎“非常的荒谬”,但亚当却“失去了……一根肋骨” (Calvin, Genesis, p.132–133)。
[46] 上帝确确实实地决定他以后再也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同上,第283页)。
[47] 同上,第286页。
[48] 同上,第177页。“极端的天气”指炎热,见Institutes 1: p. 604.
[49] 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Jeremiah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50), 5: p. 25.
[50] 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Isaiah, trans. William Pringle (Grand Rapids, MI: Eerd- mans, 1948), 1: p. 383.
[51] 同上,第216页。马科斯·特雷罗斯(Marcos Terreros)断言,对于加尔文来说,以赛亚书中所说的人与兽之间在末世的和平不过是回到人类堕落之前的状态。“Death Before the Sin of Adam: A Fundamental Concept in Theistic Evolu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vangelical Theology” (Ph.D. dissertation, Andrews University, 1994), p. 71.
[52]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1: p. 246.
[53] 同上。
[54] Calvin, Genesis, p. 104.
[55] 同上,第105页。
[56] 同上,第104页。
[57] 同上,第120页。
[58] 同上,第174页。
[61] The Works of the Rev. John Wesley (London: Thomas Cordeux, 1812), 15:149,下文简称WJW. 又见卫斯理在里斯本地震后不久撰写的论文“原罪教义”(The Doctrine of Original Sin), 来源同上,第5卷第315页。
[62] 这是一个对事物的认可过程(approbation)。
[63] WJW (1811), IX: p. 194.
[64] John Wesley, The Arminian Magazine, vol. V (London: J. Paramore, 1782), p. 11.
[65] WJW, IX: p. 194.
[66] 同上,第190页脚注。
[67] 同上,第190页。
[68] 同上,第143页。由于生产之痛在人堕落后大大增加,有人说这证明了人堕落前就有痛苦。人只能猜测之前的产痛有多严重还是仅仅是稍有不适,但是用它为借口而允许各种疼痛在犯罪前就存在似乎是轻率的。
[69] 同上,第136页。
[70] 同上。
[71] 同上,第150页。
[72] 同上,第137页。
[73] 同上。
[74] 同上,第138页。
[75] 同上。
[76] 卫斯理断言,在洪灾发生之前,地球“保留了许多原始的美丽和产能”,并且“地球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撕裂” (WJW [1811], VII: p. 281)。
[77] WJW (1812), XIV: p. 147.
[78] WJW, IX: p. 195.
[79] 同上。
[80] 同上。
[81] 同上,第196页。
[82] 同上,第139-140页。
[83] 同上,第196页。
[84] 同上,第140页。
[85] 同上。卫斯理在此敦促读者参考霍勒斯(Horace)写给维吉尔(Virgil)的第一首诗。
[86] 同上,第140-141页。
[87] 同上,第141页。詹尼斯(Jenyns)是国会议员、诗人和散文家,经常卖弄他对圣经无误等教义的怀疑理论。卫斯理对他的批评成为名言:“若圣经中有任何错误,那就也可能有一千个错误”(1776年8月24日手记)。鉴于詹尼斯的批评论调,卫斯理认为很难说他是基督徒、自然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如果他是基督徒,那么卫斯理觉得“他出卖了自己的信仰”。参见 Soame Jenyns, A Free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Evil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57), p. 15–17, 108–109; 及A View of the Internal Evidenc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London : J. Dodsley, 1776, 2nd ed.).
[88] WJW, XIV p. 150.
[89]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如果这些人看到了现代证据,他们就不会那么死板教条。但是这个问题假设了古人的解经学不如新解经学(和自然界),而且提示这些人物无法把数据整合进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此外,这些人的笔下并没有提示理性、传统或经验有与特殊启示几乎一样的权威。
[90] 若想深入理解圣经地质学家,参阅 Terry Morten- son,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2004).要看简短的、非信徒的分析,参阅 Richard Millhauser, “The Scriptural Geologists: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Opinion,” Osiris 11 (1954): p. 65–86。其他评论圣经地质学家的书目还有Jan Marten Ivo Klaver, Geology and Religious Sentiment: The Effect of Geological Discoveries on English Society and Literature between 1829 and 1859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1997); James Moore, “Geologists and Interpreters of Genesi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God & Nature, David C. Lindberg and Ronald L. Numbers, ed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322–350; Nicholaas Rupke, The Great Chain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42–50; 及 Davis A. Young, The Biblical Flood: A Case Study of the Church’s Response to Extrabiblical Evidence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5), p. 124–136.
[91] 这是 Mortenson 所讨论的30个作家中的一部分。尽管美国也有一些圣经地质学家(像 David Lord 和 Eleazar Lord) ,创世记与地质学之争的中心在英国。
[92] 由于篇幅所限,此处无法详述。请参阅我即将面世的新书 The Evolving Face of Go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Traditionalist and Accommodationist Theodical Responses in British Religious Thought to Paleonatural Evil in the Fossil Record. 参照 Mortenson的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93] George Bugg, Scriptural Geology (London: Hatchard & Son, 1826–1827, 2 vol.), 1: p. 143.
[94] Pelikan, Luther’s Works, 1: p. 73.
[95] Calvin, Jeremiah, 5: p. 25.
[96] WJW, IX: p. 140.
[97] 我无意破坏公认的人名归属,但偶尔会将卫斯理放在“ 改革家”的标签下。这仅仅是为了简洁,特指早期福音派的开拓者,别无他意。
[98] William Buckland, An Inquiry Whether the Sentence of Death Pronounced at the Fall of Man Included the Whole Animal Creation, or Was Restricted to the Human Race, (London, John Murray, 1839), p. 9. Cf. Luther’s Works, 1: p. 208; Calvin, Genesis, p. 177; and WJW, IX: p. 137.
[99] Wesley’s Works, 6: p. 210.
[100] Calvin, Institutes, 1: p. 104, 246
[101] Bugg, Scriptural Geology, 1: p. 55. 较深的初级地层里没有化石,被认为是受造岩。而许多或大多数第三纪沉积物被认为可能是大洪水后的。这些构造大致符合当今的相应分类,即前寒武纪和新生代。次生地层大致属于现代所称的古生代和中生代。
[102] Pelikan, Luther’s Works, 1: p. 206.
[103] WJW, IX: p. 253. Cf. Charles Wesley, The Cause and Cure of Earthquakes, (London: Strahan, 1750)。这篇讲道常被误认为是约翰一人的,但实际上是代表了卫斯理一家的共同信念。查尔斯认为,地震往往是惩罚,而悔改才是“治疗”。
[104] George Young, Scriptural Geology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and Co, 1838), p. 41–42.
[105] George Young and John Bird, A Geological Survey of the Yorkshire Coast (Whitby: R. Kirby, 1828), p. 342.
[106] Buckland, An Inquiry, p. 11.
[107] 同上。
[108] 同上,第15页。
[109] WJW, IX: p. 194.
[110] 同上,第190页脚注。
[111] Calvin, Genesis, p. 177.
[112] Calvin, Institutes, 1:246.
[113] Andrew Ure, A New System of Geology (London: Longman, Rees, Orme, Brown & Green, 1829), p. 500.
[114] Bugg, Scriptural Geology, 1: p. 146.
[115] 同上,第147页。
[116] 比较Pelikan, Luther’s Works, 1: p. 78, 210; Calvin, Genesis, p. 104; 和WJW, IX: p. 189–203. 在这点上路德与加尔文和卫斯理的观点略有不同,但他们都同意,野兽的本性在堕落前和堕落后截然不同。
[117] Buckland, Geology and Mineralogy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Natural Theology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1836), 1: p. 130.
[118] 同上。
[119] Hugh Miller, The Testimony of the Rocks; or Geology in Its Bearings on the Two Theologies, Natural and Revealed (Edinburgh: Thomas Constable & Co., 1857), p. 66, 69–70.
[120] John Pye Sm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oly Scriptures and Some Parts of Geological Science (Philadelphia, PA: Robert E. Peterson Press, 1850), p. 67.
[121] Bugg, Scriptural Geology, 1: p. 152.
[122] 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Romans (Edinburgh: Calvin Translation Society, 1844), p. 218.
[123] WJW, IX: p. 139–140.
[124] 这个经常被引用的短语来自阿尔弗雷德·坦尼森(Alfred Tennyson)1850年的著名诗作“In Memoriam”的第56节,这也许是19世纪中叶最流行的英语神义论著作。
[125] Stanley Rice, “On the Problem of Apparent Evil in the Natural World,”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 Christian Faith 39 (September 1987): p. 150.
[126] Bertrand Russell, Religion and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73.
[127] David Hull, “The God of the Galápagos,” Nature 352 (August 8, 1992): p. 486.
[128] Jacques Monod, interviewed by Laurie John,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June 10, 1976, quoted in Ted Peters, “Evolutionary Evil,” Dialogue 35 (Fall 1996): p. 243.
[129] Theodosius Dobzhansky, The Biology of Ultimate Concer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7), p. 120.
[130] Theodosius Dobzhansky,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Evolu- tion,” The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35:3 (1973): p. 126–127.
[131] Bugg, Scriptural Geology, 1: p. 318–319.
[132] Granville Penn, A Comparative Estimate of the Mineral and Mosaical Geologies (London: J. Duncan, 1825), I: p. 124–127.
[133] Winslow Shea, “God, Evil and Professor Schlesinger,”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4 (1970): p. 228.
[134] 潘葛洛斯是伏尔泰讽刺小说《赣第德》中的人物。潘葛洛斯博士将所有不良事物合理化,坚称这些事物在我们的“不能再好的世界”里发挥着良好的作用。潘葛洛斯主义指任何将邪恶标为“甚好”的倾向。福音派的古老地球论者是潘葛洛斯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哲学出发点在逻辑上使他们不得不认为各种古自然恶都是神所认可的。
[135] 如果要论证19世纪初的古老地球思想如何偏离了改革前教会对上帝仁慈本性的认知,那就需要另写一篇文章,但穆克(Mook)在本书第一章中对该时期的论述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健康的方向。
[136] Mortenson, Great Turning Point, p. 39.
[137] 一位进化论者估计,在这个混乱的坟墓中埋葬了8亿只脊椎动物(小的如蜥蜴,大的如牛)。尽管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是无法核实的),但卡鲁构造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化石墓地,用挪亚洪水可以很好地解释,但是用任何进化理论框架很难解释。参阅John Woodmorrappe, Studies in Flood Geology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9, 2nd ed), p. 18.
[138] 这个形象的比喻出自 Del Ratzsch, The Battle of Beginnings: Why Neither Side Is Winning the Creation-Evolution Debat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6), p. 189.
[139] Stanley Rice, “On the Problem of Apparent Evil in the Natural World,” p. 150.